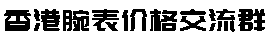点上方蓝字可加关注
微信号:十点读书
四爸
文 王东旭
我爷爷有四个儿子,父亲排行老大,四爸比我父亲小十二岁,排行老四。
一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爷爷赌博输掉了祖上的产业。为了还爷爷欠下的赌债和给还没有结婚的三爸四爸说亲事,于是,除了年龄不足的四爸外,其余的三个叔父都远走内蒙古给一户富裕的农场主放牧,两年后换回来了二十几只绵羊。后来我爷爷就在距离我们老家三十公里的一个牧场租了一片地方,把那二十几只来之不易的绵羊养了起来。等我看到时,已经是有些壮观的一群了,一百只上下,都由我四爸照看着。
四爸每次放羊的时候都会骑着骡子,我坐在他的身前,把着缰绳。到了那一片树林,我们最先做的事情就是选一块地方挖一个深坑,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我不大清楚,只看着坑里的水慢慢的渗出来,汇集到坑底而后缓慢的涨高,直到我和骡子都能够到,喝到。四爸还会在两棵树之间搭上一个睡袋,很简易的把尿素袋子的两头都拴上尼龙绳,绑到树上。我时常躺在被挂起来的尿素袋子上听四爸给我说故事,现在还能够记忆起来的都是关于鬼魂妖怪,类似于村西头的王家娃娃鬼上身,口吐白沫,每天都要枕着擀面杖睡觉云云。四爸在放羊的时候还会给我做些玩具,他把形状适合的木头雕刻成猴子的样子,猴子的四肢可以跟着绳子活动,也能翻跟头,很像城里孩子玩耍的提线木偶,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也确实见过各式各样的木偶,可是打心里觉着没有一件是比我四爸做给我的精致漂亮。他还用已经断了的自行车链条给我做过一把枪,把火柴填进去,真的就能像电视里那样发出声响和火光,而我就只是拿着那把枪,不发射火柴子弹也会在村子里掀起一股“猴代王”的威风,我自然成了整个村子里最受人羡慕的娃娃。
骑骡子放羊不论有多少乐趣回忆,但是说到底,在那个到处都是风沙,缺食少衣的农村,它毕竟是一个苦差事。我记得最清晰的一次“苦”是在一个夏天,那天突然电闪雷鸣,继而暴雨侵盆。绵羊在那样的情况下倒是显得稳定,但是我们骑的那匹黑骡子就不是那么淡定温顺,它性情大变,前蹄和后蹄轮流着扬起来,还发出我从来都不曾听到过的声音。我站在远处一边受雨淋一边哭,四爸站在另一边用尽全力的把缰绳拴在树上。也就是在一片慌乱和不知所措中,黑骡子的蹄子踩到了一只还没有长大的羊羔。我看着羊羔在泥水里喘了几口气后也就不怎么动弹了。
羊羔死了,那对于我们家来说可是大事儿,按着我爷爷的说法,一只羊羔足足能抵一家人十几天的口粮,要是羊羔再大些,那绒毛也是能做好大一块羊毛毯子。而这一切的损失都是由于我四爸的疏忽导致,于是,我爷爷拿着赶羊的鞭子在四爸身上抽了不知道多少下,四爸没有哭也没有还嘴。或许一个父亲在打骂孩子的最初,只是想得到孩子的一句软话和对于长辈权威的恐惧,但是四爸却一句软话都没有,双眼冰冷的看着前面的某一个地方。继而是爷爷脱下了布鞋,掴着四爸的脸。我已经能够看到四爸嘴角流出来的血了,脸也似乎肿将起来了,我在那一刻是恐惧并且无助的,我想要就地跪下来求情,哪怕是为着四爸挨上一两鞋底也是可以的,在之前我母亲打我姐姐的时候我都会那么做,但是那一次,我不知道是由着事情的严重性还是爷爷烧得正旺的怒火,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站在一角哭,呜咽。我至今都觉着愧疚,因着自己的胆小懦弱,四爸多挨了很多鞋底,因着自己的无担当,都不能为四爸承担哪怕一丁点的“罪责”。
第二天,天还没有完全亮的时候四爸就起来准备放羊去了,他用大手揉了揉我的肚子,在我耳边说着天气不好就不带我去了,但他说会挖好几只“跳鼠”回来,烤给我吃,放很多的方便面调料。我用惺忪的眼睛看了一眼他肿得不像样子的脸,虽然看不清颜色,但我想一定是青紫的。
其实在爷爷羊场的门前就是一片不小的树林,再前些还有一个时常有水的大水洼。按我的想法,门前树林里的草和树枝足够羊群吃,水洼里的水也足够羊群喝。那么四爸就没有必要赶着羊群翻过好几个沙丘到另一个树林去,也就不会在天灾面前孤立无援,更不会让自己受到掴脸的惩罚。他解释给我大致意思就是他最终是要离开村子到外面闯荡的,而我爷爷的年纪已经支撑不他到远处放羊了,四爸要把最近最好的林子留给他父亲。而且,只要门前的草和水洼还在,那么就不会走向死路,一旦连门前的树林和水洼都没有了,那么一切就都走向死路了。这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四爸说的话,我不知道他是经历过多少人事之后才有的这样深沉又带些沧桑的感悟,我也不确定到今天为止,我这个自称涉世很深的青年到底参透了多少,我如今确实知道的是,他绝对不仅仅是在说放羊和吃草。
四爸缓缓地拔下木门上的门插,有清冷的光透了进来。我能看清木门的蓝色以及开始掉色的门神贴纸。晨光照在四爸的身子上,他的前半面身子被木门挡着,我能看到的是后半面,一米八多的后半面,那么深重伟岸,我记忆到了现在。
二
父母离婚后,我和姐姐跟着母亲搬到了更远一些的滩里,滩里的意思就是平坦并且有充足水源的地方。我们山里人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机会在滩里置办一套平房,再在院子里种上山里鲜有的瓜果蔬菜。如今我们在父亲的缺席下,竟也奇迹般的实现了。
在搬到滩里的农忙时节,奶奶还是会赶着骡车到我们家帮忙收割庄稼。奶奶说四爸那时候已经跟着同乡的几个年轻人到城市里做小工了,就是给建房的匠人们搬砖和泥,每年也能拿回来一些剩钱。已经上了小学的我是心疼四爸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小学旁边的一所私人学校正在翻盖,我见过比我年龄大些的小工的劳累。我也是想念四爸的,我手里的玩具一个都没有了,剩下的尽是些姐姐的皮筋儿和沙包。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的“铁宝”也没有人给我做,若是四爸在的话我一定能有最好的“铁宝”打败所有人。我家那时还没有羊群要我放,但是骡子是我养的,每次把它拉到树林里喂草的时候,我也会学着四爸挖一个深坑等待有水渗出,但我还不能把尿素袋子绑在树上当睡袋,变天时,我也不能制服骡子,只是站在一旁听天由命。王来来的大儿子也曾经当着我的面摔死过我家刚出生的兔子,他的弟弟还帮腔要打我,说我没有父亲涨势。我哭着告状给我母亲,而我母亲则是以往的说辞,让我不要惹事生非,于是我就不再言语。在很多这些特定的时刻,我都想要有有父亲或者四爸在我身边守着,父亲是指望不上了,因为已经很久都不曾见过,那就指望四爸吧,哪怕他不动手,只是告诉我怎么做就好。
我是在痴痴盼望中再见到四爸的。他那时已经是个纯粹的大人了,穿着时兴的衣裳,发型也是当时很流行的偏分。我忘记了四爸那次到滩里看我时发生的许多事情,诸如我们玩了什么游戏,他给我从集市上带了什么玩具之类,都忘了。而我能够记住并且永远都不能忘记的是那一段从小卖部往家走的路。
我们村子里的小卖部只有一家,距离我们家足有二里地。那天四爸带着我到小卖部买了一大袋子果丹皮还有一袋鲜奶片和雪糕。我把雪糕塞进嘴里含着,不舍得咬,鲜奶片和果丹皮提在手上。我真的是一边儿唆着雪糕一边儿跳着走,夏天的土已经被太阳晒得虚蓬蓬的,所以我惊起了好大的一阵尘土。在路过小伙伴家的时候,我大声地叫他的名字,并把手里果丹皮分给了他一根,我故意把吃雪糕的声音放得很大,表情也是夸张了好多倍。我自豪地质问他:你不是说我没有爸么?告诉你,站在我身边的这个大人是我四爸,他在城里给我买了很多东西,你绝对没有。
在路上遇到的几个小孩我都给他们分发了果丹皮,倒不是我有多么大方,只是觉着有一种扬眉吐气的神气罢了。那天我没有碰到摔死我兔子的孩子,如果碰到了,我想我会和四爸学一招制敌的把式,把那家伙潦倒在地上,然后也给他一根果丹皮,让他别哭。
太阳已经就要落下去了,我和四爸还晃悠在路上,雪糕已经没了,但是棍儿还被我咬在嘴里,鲜奶片我不打算吃,我要拿给我姐姐。路边的玉米已经开始吐须,不知道哪里来的棉絮也飞在空中。我看到我和四爸的影子,他的是那么长,长到了玉米林子里,而我的则才能触到玉米地的畔子,两个影子相距得几乎没有什么距离。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幸福和安全感,真的,在那一刻我真的有些想要哭出来,但我没有,我还是一蹦一跳,说着我在学校遇到的事情。
我突然问四爸什么时候走,他说明天。于是,我才嚎啕大哭起来。
四爸把我背在后背,安抚着我,说一有空就到滩里看我,下次他会割猪肉,也会给我买一个电子手表,就是最流行的那种,能够当闹钟也能够调时间的。我渐渐的安静下来,看着我们两个人的影子摞在一起,更长了,已经和玉米的重叠,看不到了。
其实当我如今回忆这一个片段的时候我是极其痛苦难受的。我想,那个时候我对于四爸的渴望和需求其实是一个小男孩儿在成长过程中对于男人的渴望和需求。我不敢在学校里和同学打架,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动手,我甚至在换下开裆裤以后都不会撒尿,每次脱裤子都是脱到膝盖以下。遇到了类似于被人摔死兔子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也选择默不作声。如果说玩具这样比较物质的东西是我童年的一个缺失的话,那么成年男人对于我的引导和支撑就不仅仅是缺失那么简单了,具体要用什么词汇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些缺失不会有多么大的危害,但是有些缺失带来的伤害和影响足以疼痛一生并且改变一生。我的四爸就是时不时的在弥补我那最严重的缺失,于是,他的那种在缺失长河里留下的几道填补的痕迹就显得格外明显,怎么都忘记不了。
三
在滩里住了差不多两年,也就是我要读一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决定要去投奔已经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的大姨。由于不确定因素太多,也就无法把我和姐姐带在身边,于是,我们就被送到了爷爷奶奶家寄养。那个时候,爷爷的羊场已经倒卖,我们又搬回了满是大山的老家。
我至今都不能忘记那年冬天变态的寒冷。在霜降后的几天我就开始咳嗽流鼻涕,当年,村里的人们有个头疼脑热缓一缓就会过去,吃药打针过于奢侈和矫情,我也就硬扛着。奶奶心疼我,在别人家还没有点起炉子的时候就给我把炉子点上了,也把梨蒸了给我止咳,但一点效果也没有,我的感冒逐渐加重,发烧也开始了,终于到了必须吃药的地步。
现在说来,我都无法相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陕北农村,就真的有家庭连感冒药都买不起,我们家就是。奶奶翻遍了整个家都没能找到买药的钱,爷爷已经外出几个月,四爸打工也还没有回来,所以奶奶就只能一个人出去“弄”钱。
一夜未归的奶奶在赌博汉的身边陪赌了。(我奶奶极其痛恨赌博,因为爷爷和几个叔父都是因为赌博输尽了家产)。我们那里观看麻将的人可以跟注,押宝谁可以赢牌,叫做“钓鱼子”。我奶奶就是生平第一次去钓了鱼子,整整一夜,得了一块八毛钱:买了一袋方便面和几粒包着糖衣的感冒药。
天气比霜降时候来得更加冷冽了。学校不得不烧炉子取暖,每个学生收两块钱的取暖费。在我讲了关于奶奶的事情后,你应该能或多或少的感受到我那时候对于金钱的敏感和无奈。那一天老师通知了收费以后,我觉着我的脚步灌上了铅,整个心境也像被什么东西重重的压着、憋着。回到家,我忘记了我是否吃了饭,躺倒在了炕上胡思乱想。
我是不可能再向我可怜的奶奶开口了。我看着她佝偻的背影在收拾碗筷的时候,我就决定不会向她开口了,她为了一块八毛钱死守一夜,做了她一生最痛恨的“赌博汉”,我不知道她会为了两块钱再做出什么让我难过更久的事儿。于是,我看着已经拉上的窗帘,淡蓝色的底上画着不知道什么树,树上画着几只喜鹊,看样子还算热闹喜庆。
第二天我是空着手去的学校,和我一样的也还有几个孩子。白老师揪着我们额头的上一撮头发,把我们提溜到了讲台上,而后用画三角形的尺子重重的打在我们的手心上,每打一下,我的整个身子都颤动一下,我看着站在我身边的几个孩子已经开始流眼泪了,但我没有,我只是低着头挨着打,听着白老师说,如果明天再拿不到钱就不用来学校了。而我知道,他这句话不是玩笑,是真的。
我依旧没有向奶奶开口,她在炕上给我缝暖鞋,每次抽拉麻线的声音都是那么刺耳,像是割着我的皮肤一样。窗帘的颜色好像已经有些变化,更深了些。原本热闹喜庆的喜鹊也大都变了模样,有些萎靡。而我睡在奶奶的身边思绪杂乱,绝望的等待着时间流逝,也就在那一瞬,我竟然希望明天的太阳尽快升起,有一股鱼死网破,非死即活的绝望冲动和委屈。
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四爸回来了。他进门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用湿毛巾擦了一遍他的衣服和鞋子,四爸那天穿着一件皮夹克,很破了,能够看见有皮子已经被磨掉,露出来许多白底。他走到我跟前准备逗我,揉我的肚子。可我真的提不起兴致,他又强拉着我去和他一起捶煤,晚上烧火用。
我拿着很老式的手电筒给我四爸照着光,在电光的照射之下,他显得特别高大。四爸把铁锤高高的举起,猛地砸向一块煤,煤渣四溅。也就在那一刻我不知是哪根筋搭错了,更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说:四爸,我们交取暖费,你给我两块钱。
在我还没有缓过劲儿的时候,那个在电光后的声音沉稳的回了一句:昂,四爸回去就给你拿!
他依然用很大的力气捶着煤块,抱怨着煤渣子,月亮的光也似乎更亮了,照着我亲爱的四爸那洋气的头发。而那个拿着手电筒的娃娃,只因为幸福来的太突然而差点哭出了声音。
我当然要毫无忌惮的哭。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我没有母亲在身边,父亲更是多年不见,我倒是有一个年事已高的奶奶,她愿意为了我做任何事儿。我当然要肆无忌惮的哭,我还记得我之前破釜沉舟、“视死如归”的心境,那一分一秒于我来说都是最深重的折磨,我像是一个等待枪决的犯人被押着去往刑场,路上尽是笑话我和用蔬菜石头砸我的人,这一切的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让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哭泣么?
而我的四爸扮演着多重角色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他用两块钱在刑场解救了我,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救命之恩”不是说一说就算了的,但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具体对待,只是记忆到了现在。
我上大学的那一年,四爸包了一个很大的工程,赔了,房子都抵押了出去,为了这些,我的四婶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我在出发去大学的前不久,四爸来送我。他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年轻了,但是脸上明显多了太多我看不懂的东西,都藏在皱纹和苦涩的微笑之中。他还是叫我的乳名,摸着我的头发,并在我手里放了一千块钱,说他自己终于盼到我上大学了,然后是真诚自豪地大笑,我都能看见他被烟熏黑的后槽牙。
按着四爸当时的情况,我是不应该要那一千块钱的,但不知怎么的,我没有推让拒绝,理所当然的把钱装进了我自己的口袋。晚些时候,我送四爸走出大门,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已经有些残疾的瘸腿,虽然做过手术很多年了,钢板也取出来了,但他在工作和家庭的压力之下也就没能好利索,真的成了一瘸一拐。突然地,我又记忆起来他十七八岁那个被木门挡住的背影,也记忆起来在我最需要父辈陪伴时他背着我在夕阳下回家的影子,一时间,百感交集,只希望时间能够过得慢些,然后也虔诚的祷告,祈求命运能够宽厚对待走在我前面的这个男人。
出发去大学那天,我把我攒了许多年的打工钱和亲戚给我的压岁钱全部交给了我奶奶,一共一万。我托奶奶转交给即将破产的四爸,并嘱托奶奶务必不要告诉四爸那是我的钱。我确切的知道,我那辛苦攒起来的一万块钱与十几年前那个冬夜的两块钱比起来真的微不足道,那两块钱的恩情和对我的意义我想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还清,但是在四爸最困难,最亲朋尽失的时候,我倾自己之力帮他一把总是可以让我舒服和安慰的。
可让我不能想到的是,在来到大学的第三天,我就收到了四爸的短信,他说他感动于我给他的钱,没有白疼我,还让我多给我父母打电话,好好学习。
于是,我的银行卡里多了一万一千块钱,四爸后来说,那多出来的一千块钱,是让我消费给我女朋友的,也就是他的侄媳妇儿。又是一次没有推让的金钱来往。我回短信说了一个字,好!
如今想想,想要偿还四爸两块钱恩情的想法是多么自欺欺人。我对于四爸的亏欠从我生命的一开始就在积攒,从来都不曾中断过,又怎么能够算得清楚和还的清呢?又或者是说,为什么要去还呢?
那么就这么永久的欠下去吧,让我理所当然的欠下去吧!
四
去年春节,家里的父辈们讨论着爷爷下世以后的事儿,诸如棺材、寿衣还有坟地之类,后来又趁着要给老先人上坟烧纸,索性就一起到祖坟实地看看,挑一块合适的地方给爷爷。
那是我第一次细细的观察我们家的祖坟,有一亩多地,最南头是一排已经很高大的柠条树,紧邻着柠条树的北边儿就是我曾祖父母的两座坟冢,在坟尖儿上用砖头盖着一沓麻纸,已经被风吹得有些虚,一碰就能碎的样子。我再看已经立起来很久的大石碑,上面刻着清一色王姓的名字,当我看到我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我的心咯噔了一下,不是因为死亡或者是悲伤,而是因为神奇的血脉。原来我一直不曾思考过的血脉就在我们不经意之间稳定的流淌着,那种力量非常巨大,它不像已经被风化的麻纸,也不像已经被雨水冲刷到有细沟的土冢,它经历那么多岁月、那么多矛盾冲突、那么多人世磨难后依然静静的流淌着,流淌到我的脚边,我的膝盖下,让我不得不虔诚的跪下。
麻纸、冥币已经烧起来了,我用棍子拨弄着跳跃的火焰。我的几个叔父齐齐地用乡音喊着“爷爷,寻钱来,奶奶,寻钱来”。已经经历了些许血脉故事的我突然在那一刻恍惚了,为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的曾祖父母还有几个正在烧纸的父辈噙满了泪水。
烧完麻纸,我们跪着商量爷爷的坟址,太爷爷的后一排就是爷爷下世以后的地方,一旁留出来给奶奶。这时候,四爸说他们那一辈儿也是要埋在这里的,他要把自己的位置选在中间,两旁是他的哥哥。
四爸又突然面向我说,辉娃儿,四爸没儿子,等四爸下世以后你会给四爸烧麻纸么?
噙了许久的眼泪终于不住的流了下来。那是我成年以后第一次流泪,一时间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春节时节的风已经大了,它吹着我们坟地的柠条树硬邦邦的摆动,已经燃尽的麻纸灰也被吹起来了,吹得到处都是。我就那么留恋的望着那一片神圣的坟场,视野和心境都非常开阔。于是我想着,四爸你不怕,你下世以后的麻纸都由我辉娃儿一人给你烧,我还要带着我的老婆和孩子给您烧。
握起坟地边儿上的一把黄土,我有些释然。我深信,我终将也是要被安详地埋在这儿,前面睡着的全是我的血脉亲人。
于是,我就什么都不害怕了。
*作者:王东旭,陕西青年作者,各大文学期刊发表二十余万字,文章入选《陕西优秀文集》,邮箱:1156843660@qq.com ,微博@王东旭sust。十点读书经授权发布本文。
十点读书微信号:duhaoshu
回复“晚安”,送你一张晚安心语,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