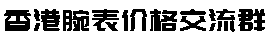1979年的9月,我正式从一个喜爱画画的乡村少年变成一名美术学院的学生。
“广州美术学院”的校牌集了鲁迅的墨迹,典雅古朴;进了大门,就看,,姿态与我几年前画过的石膏像相仿:一只手臂自然下垂,另一只背在身后,面容和蔼,神态安详,只是巨大了不知多少倍,连底座足足有两层楼高。主席风衣的下摆被微风轻轻吹起,原本巍峨的身躯就显得更加昂扬了。美院的院子里巨树婆娑、绿草漫地,曲折的石径两边开满一簇簇、一片片红的、蓝的、黄的、紫的、白色的鲜花,很容易就让人想起广州“花城”的称谓。空气氤氲滋润,与干燥单调的北方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班共12人,分别来自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和河南。初次接触,彼此间都显得很拘束,几天后逐渐熟悉,几周过了就开始嬉闹起来,外地的同学这时已经很熟练地掌握了广州人常挂在嘴边的那几句粗话。班里同学年龄相差很大,最大的26 岁,最小的16岁,背地里开玩笑时,就让年龄最小的同学给班里的大姐喊妈妈。
1979年的广州,是国内开放的前沿,是人们心目中的“花花世界”。除了街头矗立着巨幅的商业广告、小巷专治各类“性病”的纸条外,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各种走私品:蛤蟆镜、电子表、折叠伞和录音机。几个外地同学相约上街时,总觉得眼睛不够用。喧嚣亢奋、光怪陆离、生机勃勃、乌烟瘴气……这类的词用来形容当时的广州,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第一学期的素描上来画的就是石膏像。我想石膏像我是画过的,当我和同学去学校教具室搬道具,看到放了满满一屋的大卫、维纳斯、拉奥孔、被缚的奴隶、阿波罗之类的石膏像时,我不由地想起了几年前我画过的涂过清漆的毛主席。
一年级教学非常严格,完全的苏派训练方法:先画石膏头像,接着画解剖石膏头像,然后画人物头像。石膏像和人物同处一个角度,石膏像这样摆,模特也这样坐。画过几周后,石膏像搬走,模特撤掉,前面的作业上交,凭记忆再画人物头像默写,画了人物默写再画扒了皮的头像解剖默写。画一张交一张,老师一张一张打分,最后一张一张评比。
上学后学校把我们报考时交的作业退还给我们。老师说,我考大学的时候创作是中南五省的考生中分数最高的,色彩也是前几名,唯有素描不行。开始我还不太相信,私下问了其他同学,发现我的素描分数确实是班里最低的。尤其是现在一上素描课完全没辙了,不懂解剖,不理解结构,又没有经验,画的不是“脏”就是“腻”,刚入校时的兴奋没有了,我一下子就变得很压抑,很自卑,话也变得越来越少,有时甚至几天不说一句话。班里同学那阵子正热衷于相互取外号:彭俊又高又瘦,老穿条,相对于“彭大将军”,彭俊就被叫作“彭大裤子”;林若夫晒被子时被发现上面有遗精,就叫“买破(地图)”;徐坦鼻子大,成了“鼻大洛夫”;黄小鹏穿着喇叭裤,拎个录音机,“烂仔”就成了他的绰号……这时广州正上演法国电影《沉默的人》和《愤怒的人》,看电影回来,我就变成了“老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