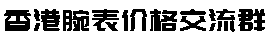5,第二种架构
李昕
在这一望无垠的白雪世界里,我俩穿着野战的那种迷彩服,尤其显眼,且这里也不安全,需要换套衣服。
北野甜递过来一个无奈哦表情。
“怎么换,这鬼地方。”
“有办法,跟我来。”我看着高山上的缆车,猜测着它要往哪个方向走,下车的地点,游乐园门口,两个人,老蔡和那个女人,跟踪。
北野甜看上去似乎有些犹豫。
“干掉那个女的,你就能重新得到老蔡。”我盲目自信的镇静,给了北野甜一点信心。
“斧头还在吧。”
“当然。”
这个雪山还挺高,幸好我和北野甜都穿的挺厚,否则光等那两个下来,估计也会冻死了。总算,总算等到了。
我们穿着巨大的迷彩服,想尽量少的惹人注意几乎是不可能的,随手在景点的商店买了两个面具,一个黑武士,一个蜘蛛侠。
我要黑武士,北野甜蜘蛛侠。
这样人们就会认为我们的装束是纯游客身份,这就好办了。
老蔡和那个女人站在街边,好像在等车,我X这种地方居然也有滴滴。
万能的滴滴真是无所不能。
我也拿出手机叫车,北野甜同时。这样才有可能跟上老蔡的节奏。
老蔡的家全是黑的,我差点昏倒。
两人在黑暗中缠绵,我和北野甜穿着笨重的迷彩服左右围攻。
女的当时就死了。老蔡吓得脸都白了。
我们拎着斧头迅速冲出老蔡家。
异世界也有警察吧,肯定有。
由于我们戴着面具,老蔡并没有认出我们。
到哪找衣服呢。
还是老办法,简单粗暴。
直接把一个服装店的玻璃砸碎了,我和北野甜居然挑了半小时的衣服,还互相咨询了意见。
她换上了一条紧身黑皮裤,黑皮衣,我又差点晕倒,但她死活不换,好吧。
我则选了一条超短裙,一件oversized的绿色大毛衣,同色系的长皮靴。
我们总算选好了一家宾馆,住了下来,脱下迷彩服真是太舒服了。
这家宾馆叫海豚宾馆。
“好像从前来过,但一下子又怎么都想不起来了。”我说
“那就不想了。”北野甜一向干脆。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每天拿着高倍望远镜,在老蔡家对面租了个两室一厅,好奢侈,住着宾馆,还租着两室一厅,我们俩的脑子可能来到异世界的时候就已经变异了。
老蔡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葬礼,女人的葬礼,又是一片黑色,我强撑着到结束。这段时间北野甜一直深情的看着老蔡。
老蔡穿黑真的很帅。
我们算计着老蔡的恢复时间,但转念一想,也不用等他恢复了,人在这个时候都很脆弱,先下手为妙。
北野甜如愿见到了老蔡。
老蔡很震惊,但在震惊之余主要还是喜悦。
我和北野甜大概编了一个灵魂转世的故事,反正就是故事会里的那种,老蔡还真信了。他接纳了北野甜。
北野甜每天忙着和老蔡甜蜜,我大多时一个人在海豚宾馆。
只是平常的一天。
海豚宾馆前台站着一个男孩,原来我记得是女的来着。
不见不知道,一见吓一跳,这个男人,居然是,竖。
他看到我也明显吓了一跳。
“你,死了吗?”他小心翼翼的问。
“啊?我怎么会死?”
“那你怎么会在这里。”
“怎么一定要死掉才能来这里吗?”
竖一脸茫然,估计他不知道来到异世界的入口,但他又是怎么过来的呢?
没多久,我就搞清楚了真相。
原来异世界的入口分好几种,其中一种就是过来的,而竖就是这一种。
“他还是了。”我有点难过。
“你为什么⋯⋯”我明知故问。
“不知道,说不清。”竖典型回答问题的方式。
他甚至没问我是怎么来的,这也很像他。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啊”我很委屈
“真不明白,你们女人,我永远不明白。”竖更瘦了,脸颊上的骨头都明显塌陷了。
“你以为是那此我们没搞,我生气了,其实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个。
“我知道,韩梅跟我说了。”
“你真正爱的是陈眠吧?”
这个问题竖想了很久。
“好像也不是,只是因为大家在一起没什么负担,她不需要未来,你要。”
“是因为这么说会让我好过一点吗”
“不是,你了解我的。我懒得撒谎。”
竖守着海豚宾馆,好像还挺适应。
北野甜和老蔡在一起,重新焕发生机,快乐无比。
我因为竖在这里,也不急着走。
直到有一天北野甜一脸沮丧的来了。
一开门她就抱住我哭了。
“原来还有一个北野甜,怎么办?老蔡完全分不出哪个是我?真正的我?”
“可能是他一直都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你,而不只是在异世界。”
北野甜听到这个,沉默了很久。
“无所谓,再干掉就是了!”我拽出藏在床底的我们的大红斧头。
我们趁着假北野甜下楼买水果,一把把她拉到了一个小巷。
一斧头就割断了颈动脉。
当场死亡。
连尸体都懒得管,反正咱还有一个北野甜。
穿黑皮衣皮裤的北野甜拿着一塑料袋香蕉,一塑料袋葡萄,走向了老蔡的房间。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解决衣服问题的,但我相信她肯定能圆得过来。
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我和竖渐渐比原来熟识了,从前在那个所谓的现实世界,我们有太多的误解。
我的心情越来越好。
不过也没好多久。
一天晚上,我去看了北野甜那边的情况,还算稳定。
踏实回到了宾馆,远远地就看到竖跟一个女人,坐在前台聊天。
而这个女人,就是“我”。
我立刻傻眼了。
马上拿出手机电话北野甜。
当天晚上我们蛰伏在宾馆斜对面的咖啡馆,静等女人离开。
晚十一点十分,女人在等车。
车还没来,到对面服装店逛。
只需要过一个直线距离,几十米。
我和北野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个捂住了女人的嘴,一个用斧头顶住她的腰。
又解决了一个。
我们发现异世界有一个好处,杀人不犯法啊,或者干脆没法律。
竖又是我一个人的了。
我和北野甜在异世界过的其乐融融,她和老蔡,我和竖,我们甚至还经常来个四人约会。
但好景不长。
异世界是个四维世界,也就是说每一个维度的人都可能抵达这里,我能,北野甜能,其他人就也能。
只有一种情况不行,死去的人。
比如老蔡和竖,在原来的世界也好,异世界也好,都只有一个自我。
而北野甜和我则是无限的,如果是四维的话,就至少有八个,除了我们俩,已经干掉了两个,还有四个。
四个隐患。
6,割裂
甜老虎
兔子说我小时候被割掉了。
我回到车内,对小昕说。
我们在滑雪场外。雪崩过后恢复正常。仍然有游客前赴后继去死。这些游客里都有着循环的脸。(就像我跑步时看到的那样)。
割掉了什么?
小昕问。
割掉了我与现实的联系。
点头。
兔子说,回去。很难。
难吗?难的并不是回去,而是回去以后怎么办。
对的。疯了以后就不能假装自己没疯。
这些倒也没什么。你去了那一头了吗?
那一头?
是。设定成去不成的那一头。
去了。我把她们都杀了。
我这才注意到车厢里都是血。
不是说,那一头没人到过么?
我很容易就到了。我到了以后,就跟解开了什么封印似的,游客蜂拥而至。
他们大呼小叫,抢夺房间。很难想象濒临的人有那么大的热情。去疯抢一个个雪地小屋。
用来。
是。
反正都是死,杀了他们更好些。
大概吧。
沉默。
小小微光,伴我闪亮
小小微光,伴我闪亮
小小微光,伴我闪亮
小小微光,伴我闪亮
……
音乐声再次响起,像是在催促我。
那我也得去一下吧?
下车,踩着吱嘎吱嘎的雪,我走去观光缆车。
这是异世界的设定。说成是游戏设定也未尝不可。异世界的第一层,就是这个玩法,坐观光缆车去另一处,杀掉你想杀死的人。第一次我想杀老蔡失败了。我经历了一次崩塌。然后我再次来到这里,小昕完成了她的任务,我只能重复第二次。
游戏是可以重建的。可以反复。无数次。游戏是极其有耐心的。异世界应该也是。
我坐上观光缆车。缆车上往下望,小昕在抽烟。车窗开着,一只兔子站在车外跟她说话。从我这个角度看,兔子是有轮廓的,不仅有轮廓,而且有鼻子有眼,无比清晰的三维立体兔子,脸上的兔毛都纤细可见。
而我的兔子呢,那个眼睛是黑洞的家伙。
脚下的脚印是红的。那是血。
小小微光,伴我闪亮
小小微光,伴我闪亮
小小微光,伴我闪亮
……
依旧是老蔡的历届女友。纷纷摔断了脖子死在雪地上。再往前。是老蔡,他是上一个游戏的残留物,并非真正的死亡。只是一个残留物,思维还未来得及清除掉的。
再往前,横七竖八的陌生人,死着。
再往前,雪地里的小屋,到了。
我很容易地走下缆车,走进小屋。整个雪原一片静谧。
小屋里等着我的,是我爸。
白色的墙壁。雪屋里什么摆设都没有。
我爸拿着一条黑黑的影子。他站着。
我知道那是什么。那是被他割掉的我和这个世界的联系。
你能把那个东西还给我吗?
我问我爸。
它已经死了。你要它有什么用。
我爸冷冷的说。
它已经死了。你拿着它有什么用。
我反问。
我不拿着它,它就没了。
我爸说。
那你给我吧。
我走过去,抢他手里的黑影子。
你为什么要割掉我?
我突然爆发。为我爸的不知忏悔。
你不知道这里的雪屋都是为你们而建么?
我抓起挂在墙上的斧头。
把它还给我!你们这些不知悔改的人!
(这些伤害过我的该死的)。
我嘶吼。
那条黑色的影子软趴趴的。我能写无数黑故事纪念她。
她的轮廓仍然是一个死去的小女孩。
把她给我。
已经死了。
把她给我。
早就死了。
你为什么要弄死她?
算了,我根本不想知道你为什么弄死她。你这个自大狂。
我抢夺那条影子,那是一条封死的路(小径分叉开满了歧途的花)。
我把我爸劈死了。很快。
他没怎么反抗。他用他特有的不理解的眼神看我。胸口插着那根斧头。
他这辈子都会这么看我。
那条影子从他手里抢过来,在我手中逐渐变浅,变成灰色,透明,最后,滴了一滴水在雪地上。
消失了。
任务完成?
我不知道。
我带着满身的血坐缆车回去。
第二个隧道有什么呢?
坐在缆车上我想。
您抢回来的是您的尾巴。透明的兔子说。身边左侧陷进去一块,应该是兔子坐在我身边。
点头。
它已经连不到您身上了。
您的父亲毁了您所有的现实感。尽管您一直在否认。
点头。
异世界并不能重建。它不是心理架设。
点头。
死了就是死了,您父亲说的没错。
点头。
您可要在这个故事中诠释这条影子对您的重要性的。
点头。
小小微光,伴我闪亮
小小微光,伴我闪亮
小小微光,伴我闪亮
小小微光,伴我闪亮
……
我浑身都湿透了。不知道是血还是雪还是我的眼泪鼻涕一类的。
我在哭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种哭就像是在梦里哭。电缆一根根在我身后垂下来。血水从我身上往下淌。那是我爸的血。也是我的血。我是他的女儿。
我做到了。
我做到了这么多。
你看,我做到了。
我做到了我厉害吧。
老蔡从地上爬起来想爬上我的缆车。他往上伸出手,我往下伸出手,我要拉他上来。
可是他滑下去了。
滑下去肯定摔死了。
电缆观光车咯噔一下。
下一个电杆旁边,又一个老蔡在挣扎着站起来,朝我伸出手。
我再次猫下腰也伸出手给他。
他再次滑下去。
咯噔。
我做到了。
我对脚底下的老蔡喊。
老蔡仰着脸对我点头。他的脸虚胖、浮肿、不像他。
老蔡浑身是血,唯有脸上一丝血迹都没有,健康,正常的一张男人的脸。
手一滑,他摔下去。
我砍了他。
我一句一句说给他听。每次摔,只能说一句。
好在可以无限循环往复。
每次摔下去之前,我都可以告诉老蔡一句话,一个感受。
他仰着无限正常的脸。
摔死你吧!
我终于喊出来。
死律师!
混蛋!
去死吧!
你们一起去死!
我的血不断地滴在他脸上。他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波澜不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雪地上是我癫狂的笑。
我可能回不去了。
是呢。您这样下去是回不去了。
兔子也这么说。
您跑步的时候也经历过。跑着跑着就迷失在时间和时空的夹缝了。
这个夹缝,到底是什么?
我只是随口一问,我才不关心这个夹缝究竟是他妈的什么。
浑身淌血的我淌的很爽。这样淌着血,在雪地中,不会疼,不会冷,还能不断地啐前男友,还有比这个更爽的事么?
我冲兔子喊。
您冷静些。小昕还在等您。
兔子严肃地说。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她可以召唤卡夫卡陪她!
您确定您要在这冰天雪地里啐他一辈子么?
兔子问。
发呆。
我确定要在这冰天雪地里沾满我父亲的鲜血一而再再而三地啐我前男友么?
我还想要点酒。我对兔子说。
脚下被一只手抓住了。老蔡要爬上来。
十二点一过,所有的死尸都要变僵尸呢。
兔子说。
怎么可能,你当这是美国电影么?
我看了一眼我手上的电子表(我什么时候有了一块卡西欧的电子表?还是橙色夜光的?)。
十一点四十五分。
雪地变得绿莹莹的。无数眼睛在雪地里闪烁。
我不太相信兔子说的,眼看着,老蔡就要爬上来了。
老蔡,我把你带回家吧。那怕把你改造成充气娃娃,那怕把你改造成人工智能人,我还是能一样爱你的。可是,你现在这个浮肿而又正常的样子好讨厌啊。
一脚踹下去。
小小微光,伴我闪亮
小小微光,伴我闪亮
小小微光,伴我闪亮
小小微光,伴我闪亮
临近结束的音乐响起。
远处亮起车灯,小昕一定等的不耐烦了吧?
紧急制动扳手可以让缆车加速。在尸体变僵尸之前。
僵尸啊!潜意识创造的世界太俗气!
雪地上那些女孩站起来排好队。
准备跳舞么?
守着一个不再是男友的男友,淌着父亲身上的血。
北野甜,你不腻么?
十二点,电子表滴滴滴滴,又是震动又是响,老蔡再次爬了上来,扑向我脖子。
我被扑倒在雪地上,那些女孩蹒跚着走向我,老蔡开始咬我脖子,我被摔得动弹不得。
老蔡撕咬我,脸上的正常消失了。
他真陌生啊!
7,另一种割裂
李昕
“真希望一觉醒来又回到十四岁以前,嗯,不醒过来也行。”我喃喃地对着北野甜说。
这应该是真心话,无数次我准备开煤气,但都因为不懂如何正确操作而放弃。
也不是懂不了,大概并不是真想死吧,或,还没做好准备。
每个清晨醒来,都觉得这一天是赚到的。
我不断吃着格力高超细装饰饼干,巧克力,和奥利奥威化饼。
我感觉到一种甜正在侵蚀我。
一个胖子悲惨的死去,简直有娱乐效果,但如果是一个瘦子,人们的反应就会比较平静。
瘦让人觉得正常和平静。
我也想过,那些兔子,它们之前是什么,之前的之前是什么,直到它们成为以人体为宿主的胚胎。
紧接着我又想到了爱丽丝漫游仙境的兔子洞。
神秘的兔子洞,整个小说只是寥寥几笔。
兔子洞从哪来的,为什么会在爱丽丝家里,又为什么能起到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作用。
在多维世界里,人的确会变得更混乱。
我和北野甜最近都很紧张,因为四个我们的关系,我们既想遇到他们,杀掉他们,又有些害怕真的面对这些,所谓的自己。
我们定期约好在海豚宾馆商量此事,但又不能被老蔡发现,所以只能是夜里,但这里又没有夜晚,就只能按照老蔡的生物钟来设定时间,实在不行就来几片安定。
这个办法我们从前就用过。
我和北野甜坐在两人标间里相对沉默,没有太好的办法,但可以先捋顺头绪。
其余的两个“我”,两个“北野甜”,我们甚至不知道她们在哪里。
“要先把她们印出来。”我沉静说。
北野甜点头。
按照异世界的规律,一个人消失,就会有另一个“同样”的人补上,但时间不确定,所以我们最终还是会达到目的。不过问题是要等到什么时候?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肉桂粉,我们从地下拿来的肉桂粉,肉桂粉可以吸引一切异物质,包括人。
这是我们走时兔子们送的礼物。
“总有一天可能用到,您就拿着吧。”绿领结德国腔的兔子手里是一包粉红的小纸袋。
“但您一定要记得用法,肉桂粉是有灵魂有生命的,不能随随便便的用。”兔子又叮嘱道。
“一次只能用四分之一,兑绝对伏特加可以用三分之一”
“两次用的间隔必须要有二十天,连续无规则使用会发生难以预料的结果,总之是不好的结果。”兔子慢悠悠说。
“听说您和甜老师要去异世界?”兔子仿佛现在才切入正题。
“嗯⋯⋯”兔子沉默了一会。
“您可能会有惊人的发现,在异世界会发现地下的秘密。但是否有机缘,要看你们自己的行为和磁场。”
正常的话,我和竖在一起,北野甜和老蔡在一起,那么另外四个人就很难出现了,至少时间无法确定。但我想到了肉桂粉,包裹肉桂粉的纸张反面,写着另一些“规则”。
“你把伏特加兑肉桂粉喝了,然后再去拿给竖,设法让他喝了。”我对坐在对面的北野甜说。
“我则重复同样的行为,我去找老蔡。”
北野甜惊讶地望着我,她的眼睛本来就细长,身体也是细长,但一显出惊讶的表情就更细长了,像一条柔软的丝绸,长条的那种。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北野甜扔掉手中也是细长的爱喜,站了起来。
没过多久她就回来了,竖很爱喝酒,对竖来说,让他喝掉含有肉桂粉的伏特加并不难。
但老蔡就有难度了。老蔡不喝酒。
“我尽力吧。只要我们把这一切反过来,打破异世界的秩序,另外的小昕和北野甜们就会按捺不住出现,到时就看我们的了。”
对老蔡我实在没办法,只好简单粗暴了,先用安定弄昏,然后绑起来,意识时而清楚时而不清楚,我趁机给他喝了兑肉桂粉的伏特加。
喝完他就头一低,又倒下了。
一切都准备就绪。
只差那几个婊子出现了。
喝了掺杂肉桂粉的竖和老蔡,都把我们当成了小昕和北野甜。
到这里情况就是:竖和北野甜在一起。我和老蔡在一起。
这一招果然管用,甚至连这里的极昼都貌似产生了某种变化,我觉得天好像没那么亮了,不过也可能是幻觉。
我们日夜守着竖和老蔡,到哪去都跟着,只差男厕所了。
“很奇怪,你的身上有种熟悉的味道。”竖对北野甜说。
“很奇怪,你的身上有种似曾相识的味道。”老蔡对我说。
我们粘了竖和老蔡足足四天,精神紧张,随身都带着一个大包,纯黑的双肩包,里头有我们大红的斧头。
第四天晚上,或者说白天,一个“小昕”终于出现了。
“看来你比较不能忍。”北野甜诡异的冲着我笑。
我知道她说的不能忍是什么意思。
一个全黑的小昕,为什么哪哪都有黑色。
她远远的观察着竖和北野甜,我则远远的观察着她。
她行动敏捷,好像练过搏斗术之类的,有点危险。
北野甜夜里十点离开竖,前往海豚宾馆304房,安全起见,我们开了两间房,对着的两间,304和307。
黑衣小昕很快就站到了北野甜所在的房间,手里拿着一个类似刀片的东西,我在走廊尽头看着,我已经示意过北野甜,正常情况她应该拿着斧头躲在门后了。
我等着接应。
门开了,黑衣小昕走了进去,我只听到一声惨叫——
妈的是北野甜的,我连忙拎着斧头跑过去,这个小昕有点功夫,绝对是练过,但我们毕竟是二比一,她越来越难以应付拎着两个大斧头的我俩(这个情景很有喜感),竟从窗外的树爬出去了。
跟黑猫似的。
北野甜坐在床上喘气。
“这个比较难对付,等最后再解决她吧。”北野甜喘着气说,尚未回魂。
老蔡每天被我用安定搞的迷迷糊糊,好像比竖更容易看管,北野甜没花太大力气,就等到了北野甜二号。
我们一人守着单元门的一边,这个女人不像小昕二号,我们终于松了口气,她还没来得上楼梯,就被我们几斧头解决了。
先砍的颈动脉,连哼都没来的及哼一声。
“老蔡和你,又近了一步。”我给北野甜打气。
“再除掉一个就可以了。”我像是对北野甜说,也像是对自己说。
在等待小昕三号和北野甜三号的时间,我们无所事事,整天逛着没人的商场,这里都是无人收费,倒挺先进的。
抓娃娃,这种弱智游戏居然也有。
我们直接用斧头把娃娃机敲碎了,异世界仿佛很富足,除了保安不好,没有警察,全是白天之外,简直可以说是个完美的世界了。
好像每个人对其他的人都没恶意,太奇怪了。
所以严格来说,这个世界只有两个罪犯,我和北野甜。
牛逼的独一无二的两个。
完美拎了一筐娃娃,在回海豚宾馆的路上,一个一个的把它们抛在天上玩,看谁扔的最高,好无聊,但我们玩的很认真。
北野甜的屁桃君挂在了一棵大树上。
实在爬不上去,我们只能砍树,砍啊砍砍了很久,终于把树砍倒了。
这时我听到一丝异样的声音。
“你们不能乱来!”一个严肃的男声。
“是谁?”我们慌张的四下观望,还是没看到任何人,天还大亮着。
“想象星巴克咖啡馆,肉桂粉,地下,除了你们还有谁⋯⋯”
我恍然大悟,是卡夫卡先生。
“您不是在地下吗?”我诧异问。
“这里也是地下,只不过是地下的地下,你们居然还不明白。”卡夫卡,或者说倒下的树低沉的说。
“你们扰乱这里的秩序,就会改动兔子们世界的秩序。所以说,请不要乱来!”
“进入这里的入口有两个,一个是星巴克,一个是cozy。”
“那⋯⋯,那个现实,世界呢,是地上还是?”我的脑子彻底乱了。
“没有那个世界,那个世界是幻觉,在那个世界的你们也是幻觉,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卡夫卡的声音越来越严厉。
“但我们必须要做这件事啊,老蔡,竖⋯⋯”我难过的低下了头。
“你们以为你们杀死了其他四个,就能和他们永远在一起吗?”卡夫卡的声音逐渐微弱。
“啊?!”我想追问下去,但卡夫卡明显已经不在了。
“这怎么回事?”我问自己,向着北野甜。
我和卡夫卡先生对话时,她全程沉默。
“我好像理解了。”北野甜低低的说。
“理解什么了?”
北野甜三号出现了。
在海豚宾馆,她藏在大堂一堆沙发里。一大堆血红的沙发。
这当然难逃我们的眼睛。
打烊后北野甜把竖哄进房间,在前台打开黑色的双肩包,拽出斧头。
但她晚了一步,我先把这个婊子干掉了。
很容易,甚至没用上斧子,就用了一条黑丝袜。
她的眼睛还圆睁着,似乎想对我说点什么,但我毫不留情的勒死了她。
拖到宾馆厨房,厨房下有个地下室,我和北野甜早把这里霸占了。
放上案板,分尸,放进黑色垃圾袋,再打车去江边,一袋袋扔掉。
我们在江边举杯庆祝,起码先把多余的北野甜们都干掉了,我们其中的一个,安全了,可以放心拥有自己喜欢的人了。
但在北野甜三号被处理掉的第四天,就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
小昕二号和小昕三号同时走进了海豚宾馆。
两人身穿一模一样的衣服,黑色皮衣黑色紧身裤,还戴着黑色面具,可能因为我是本体的缘故(或我自认是本体)还是把她们认了出来,我和北野甜藏在307房,商量对策。
商量的结果是没有结果,没有太好的办法,我拿出了肉桂粉。
“只能再用这个了,还是四分之一,兑伏特加。”
北野甜点点头。
我们轮流把门推开一条小缝,观察那两个小昕。
小昕二号三号直接上了三楼,没用电梯,一上楼,两人就摘下了面具。
我的天!
他们不是小昕二号三号,他们是小昕二号和北野甜三号。
但北野甜三号不是死了吗?
“什么?”北野甜差点被咖啡呛了一下,“怎么会?”
我们怎么想都没想出来,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在想到筋疲力尽时,咖啡也不管用了。我们鼾声睡去。
第二天我一睁开眼睛,就被吓了一大跳。
北野甜睁着极为细长的眼睛,像两条蛇,它们定睛的看着我。
“除非是小昕二号和北野甜三号合体了。也就是通过磁场链接的方式,合为同一个人,三号才会活下来。”
合体这种事,我是听兔子说过的,这也是它们从前霸占了一个童话作家的故事,给自己设置的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人和人是可以合体的,结果是更强大也更脆弱。
果然。
合体的小昕二号和北野甜三号,正在这时,把我们的门踹开了。
我们甚至没时间去拿斧子。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看上去是。”小昕二号冷冷地说。
北野甜三号也是同样的一副表情,像挂在冬天松树上的冰霜。
“知道什么?”我胆战心惊问。旁边的北野甜也一脸困惑。
“你们是从虚拟世界来的,所以我们杀不了你们。但可以给你们提个醒,不要再这样做下去了,这样下去对你们只能是有害无利。”
小昕二号和北野甜三号对看了一眼,利索的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衣服,好像衣服上有很多灰似的。
我一脸茫然。
茫然到都没注意北野甜趁着我们说话没注意,偷偷溜了出去。
两人成功被堵在楼梯口的北野甜用双斧砍死。
她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她们杀不死我们,但我们能杀死她们。”北野甜此刻的样子像极了刚才那两个人。
“小昕二号不是有些功夫吗?”
“是因为和孱弱的北野甜三号合体,削弱了力量。”
也只能这么解释了。
现在只剩小昕三号了。
唯一的隐患。
我们更加全神贯注,不能功亏一篑。
至少北野甜们都死了,还是那句话,值得庆祝。
我们坐在那棵被砍掉的树下,想着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我说你们真是屡教不改啊!”
卡夫卡。
“什么情况都不知道,鲁莽行事,你们当真是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吧?”卡夫卡先生的声音越来越尖利了。
“什么情况,告诉我们,小昕二号似乎也说过这种话。”
“到最后你们就会知道了,唉⋯⋯”卡夫卡叹了长叹了口气。
“无论如何我都要和老蔡在一起!”北野甜哭了,但哭的坚决。
“我也是。”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都不后悔。”
“嗯。”
我们又像前几天一样,分别看住竖和老蔡,静静等待着最后一个小昕。
“在地上那个世界,哦对,是他们说的那个虚拟世界,真的是虚拟就太好了,每一天都过的很困难,每天都想死。”我和北野甜坐在307聊天,喝着伏特加,但没兑肉桂粉。
“是啊,如果真是那样是太好了啊。但我们之前不知道,以为那些都是真的,确实伤心来着。”北野甜拿起伏特加,猛喝了一口。
“所以你和老蔡并没有分手。”我说。
“所以你一直是和竖在一起的。”北野甜说。
“我们来之前,兔子好像在暗示我什么,异世界的秘密⋯⋯”
“嗯,这里的世界,和兔子们的世界,我也搞不懂了,只能说是多维世界,但多维也可以有穿插是吧?”北野甜放下了手中的酒杯。
“不对,兔子的意思好像不是这样。我说不清,它们之间肯定有联系,但是是通过什么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卡夫卡先生也会在这里?”
“这一切都是个谜,我们要解决的,不止是那个小昕三号。”北野甜咕咚咕咚把杯子里的酒都喝了。
我则拉开窗帘,看着天上永恒的太阳。
在此时,它只是一个白到刺眼的圆圈。
8,诠释1
甜老虎
睁开眼的时候我在小昕的家中。怎么来的我已经不记得了。
小昕的家里有股牛奶和茉莉花混合的光线。我躺在她床上。
我杀了我爸。我把老蔡从缆车上踹下去。我踹了无数次。我还骂他。
后来我手上的手表滴滴滴响了起来,那些尸体变成僵尸。老蔡爬上电缆,咬我,她们撕碎了我。
我对小昕说。
小昕点点头。
我冲进雪地,你躺着的地方聚集了方圆几百里的僵尸。
我被啃成白骨了吗?
差不多吧!
你是怎么把我弄出来的。
我有枪。
点头,我信。
小昕拿出一条项链,递给我,项链上有个佛头。
戴上吧。
我有个一样的戒指。佛头。
我接过来。
我还有个戒指是把枪。我把这俩戒指并列戴,枪指着佛头。
我比划着。
记得还写过一个短故事,叫《佛头》。
你在地下有个住处?
回过神来,我问。
有。
有兔子的地方就有。
我发现我有瘾了。烟瘾还有别的瘾。
我塞了塞被角,小昕的被子很软。软的不得了。白粥一样的光线在她家里飘忽,一只肉色的兔子在阳光照射的角落一个劲地翻跟头。
发条声咔哒、咔哒地响,有光斑在地上。
好一点了我们去楼下荡秋千。我们喝了咖啡,我指着纸篓里的咖啡包装条说起《恐怖游轮》,电梯里小昕说起蓝可儿,我讲起我做的一个梦,梦里有楼顶的水箱和巨大的九连环杀人机器。
一对双胞胎在阳光下站着。秋千旁。
小兔崽子这个词无数次在她小说里出现,这次是她用嘴巴说出来。
小兔崽子。
这俩小兔崽子太小,还荡不了秋千。我们坐在上面。
闭上眼的时候眼皮感受阳光的照射,忽明忽暗,眼皮的肉色一会明亮一会斑驳。渐渐地斑驳变成条纹一条一条在眼皮上。头颅在晃动。
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抽烟。
我们去星巴克。两个人的星巴克。
上了她。
小昕说。
星巴克像个婊子在等我们上她。
是这样的。我们已经把她写成了个烂货。
周六的星巴克人特别多。霸住一张桌子。两杯拿铁。走来走去的人,确实比我创造的世界热闹的多。
这里已经自成体系了。不只是一个房间,简直是小半个城市。
我对小昕的创造力非常佩服。
(那只翻跟头的发条兔是不是还在家里翻跟头呢?)
咔哒咔哒。小昕家门口有个灯总是发出滋滋声。
滋滋滋滋,咔哒咔哒。
这些声音汇入某种能量。
我的包里有粉色的盐(据说可以招桃花)。
星巴克的椅子上有个女包。
黑白斑纹的女包。
滋滋滋滋。
隧道雪地恢复寂静。小小微光伴我闪亮。
我上瘾了。
女包。香奈儿。重重的链子。你猜它是真的吗?
铅笔,票据,身份证,银行卡。这太他妈的真实了。
这是真实的星巴克。这是真实的星巴克吗?
我连不上网。
跟小昕在一起的时候我很想脱衣服。倒不是。大概属于想裸奔那种。
在秋千前面的长椅上想过一次。现在是第二次。
她坐在我身后,我俩背对着背,电脑开着。我们都在写。
她说这叫文字性唉。
空气里分子都不对了。我说磁场会改变。我说想要钱只要不断地想就好了。
我疯了。
我的兔子不这样认为。
您早就疯了。只是现在才刚刚缓解。
兔子说。
兔子坐在我身边,穿了兔子连体衣的,兔子?
杭州很冷。兔子说。
点头。
小昕很酷。
点头。
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我上瘾了。不知道是对小昕还是对另外这个世界。 不进入它,我就浑身不自在。
我说过您出不去了。
兔子说。
我总觉得,我还是能摸到那个缝隙的,就像死了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死了。死后的那个世界充满了生前世界的蛛丝马迹,就像那个香奈儿包,里面还有他妈的奔驰的车钥匙。这一切绝对预示着有事要发生。
要不,跟小昕睡了吧。
兔子说(也可能是我说的)。
突然瞌睡的不得了。大脑出现了某种舒服的抽搐,我想身后的她大概在写我。脸上有模糊的嗑药般的微笑……
胸口疼。
对咖啡的依赖越来越少后,对烟的需求量激增。
小昕总是说,来,抽根小烟儿。
俩人坐下,一根接一根。
一只兔子死了。它的皮做成鼓,被其他几只兔子捶。
原始鼓点响起的时候,社会性逐渐退去。我和小昕待在异世界,怡然自得。
你所惧怕的其实就是你自己。
你所惧怕的是被自己毁灭。
而我,我要竭尽全力去寻找那个通道。找到我自己。
找到之后做什么?
跟自己待会儿。
嗯。
待会儿。
我千山万水。穿过一个个隧道,跑来异世界,跟自己相遇。
凭我自己的本事都不行,我进不去。兔子说过,我找不到那个入口。
现如今。我进来了。我身处这个联系中。它是个联系。联系是什么意思呢?
你把移动硬盘用数据线插入电脑的时候,你的移动硬盘就会和电脑产生联系。对,就是这根线。
我待在这根线中。
我能往那边去,那边是黑盒子。黑黑的。存储了大量数据。但我回不来,这个路径过于漫长。
您太没有耐心了。
兔子坐在我身边。后背缺了一大块。
你的皮?
兔子点头。
这样也行?
行的。
兔子满不在乎。
那只鼓?
给孩子们玩玩。
兔子说。
房间又亮起来,肉色的兔子在翻跟头,咔哒,咔哒,这个声音让我觉得异常安宁。
咔哒咔哒。我开始觉得放松。我脱掉白色的睡袍。想裸就裸着吧。
去诠释这里面的关系,感觉特简单似的。三言两语就说尽了。
我跟小昕说。
我跟世界的关系,我跟我自己的关系,我跟你的关系。
我补充。
还不够。小昕说。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很多。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毕竟这个世界只听我们的。
你有这个能力(能量)。
我继续抽烟。
你也可以(把手放在我手上,第一次肢体接触,除去那次分离前的拥抱。)
她离我太近的时候我的脸总是发出抽搐。
那是一种北野武式的微笑。
我点头,释然。世界的疯狂不过如此。
当我全部接受了我的疯,这个世界的黑终于阖上了它的眼睛。不再企图白,或者把自己漂白。也不再承认自己的弱,弱和强都是一些狗屁法则。疯了挺好的。我常年躲避的东西,不过如此。
如此想来,或许我跟小昕患有相同的病症。我们都有一张会员卡,一张黑色孤儿通行证。不在乎谁拷贝谁的,也不在意谁写了谁,我们原本是同体,一定是这样。
我遗失的部分生长在她这里,这些年,她把这些东西照看的好好的。我又愿意写童话了。这真不错。
无数障碍一下子跟打通了似的,我知道这是幻觉,它们就藏在门外,或是藏在数据线那头,但我不在乎,我可以打它们,打败打不败的,已经无所谓了。
小昕有枪。
嗯。
我的长句子又回来了。
长满荒草的庭院又回来了。
那些塑胶人,种在地上,孩童在他们之间喊话。
杀人狂是我的邻居。
有昂贵音响的杀人狂。
开滴滴的也是我的邻居。
异世界住满了人。寂静无声。
为什么要抗拒呢?你原本就住在这里。兔子在摸我的膝。
胸口插着斧头的父亲坐在我身旁。
老蔡在门外爬来爬去。
那些女朋友们,她们待在麦田,是一个个布娃娃稻草人。
太阳出来了。还是有雾。不过不碍事。一切会好。
已经很好。现在这样就挺好。没有糟糕(糟糕在另一头)。
没有糟糕,没有糟糕。
尼尔·唐纳德·沃尔在收音机里说。
小川挂在电网上。
原谅你的罪恶吧。和你的恐惧,握手言和……(言你妈逼的和)
我走过去关掉收音机。
异世界的第二层,我们还没走过。不过我现在,更想跟小昕走进那个地窖入口(头朝上走着走着头就朝下的地窖)。我知道,打开门,门外即是星巴克。
我脸上,北野武式,抽搐,微笑。
对啊。您是可以回来的。
我的兔子说。
9,诠释2
甜老虎
原罪要在哪里找?当然要在现实世界里找。
电脑联通网络,移动硬盘只是电脑里的文件的复制品。
复制品当然也可以营造一个世界。只要你疯的可以。
我现在就疯的可以。
我和小昕约了,见了,我们戴了同系列的心形耳环,这种乡村名媛式耳环被我们戴出了摇滚诗人范儿。
我们点一样的牛扒。喝同一种咖啡。
我们见面了。
嗯。
事情发生在星巴克事件以前,异端出现在星巴克事件以后。
事件以前我去了她家,睡了她的床(她不在床上)。回家后我开始在公号更新《星巴克扮鬼事件》,更到第三的时候,我翻朋友圈,以为自己看错了。
我看到一个恍惚的自己。也在推一篇文,名字叫《星巴克****》,紧接着,辫子发微信过来,你和小昕都在星巴克搞事情。
连推送方式都是一样的,没有多余文字介绍,赤条条一个公号文章推出去。
我的叫《星巴克扮鬼事件》。她写了《星巴克失踪事件》。
我被吸引了。
虽然都是星巴克,她的和我的迥异,但,我仿佛进入一种内循环,我感到自己被拆碎了,一个颗粒一个颗粒,被放置入她的故事中,与她共生。
一篇一篇的更新,她跟进。
这种感觉,应该叫奇妙。
小昕说。
我却一直在说,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是太爽的代名词。
我完全被那个地下那个世界吸引了。
无奈我的星巴克扮鬼事件是三年前写的。而她,每天都写一篇,星巴克失踪,我们的思维,在小说中暗合,毫无刻意的成分。
你看,我这样一解释,就没意思了。
所有的原罪都出现在生活中,我的兔子对我说。
办公室,寂静无声。如果没有小昕,我不会来杭州。
不不不,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空气中的某些成分,为我来杭州(不管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都做了重新组合。
那些白乎乎的光线。
那些黑乎乎的扑下来想黏我鞋底的东西。
我对变成颗粒上了瘾。自我被完全打碎,进入另一时空重组。
那里比现实世界好玩多了。
肉桂粉不再是肉桂粉,它是肉桂粉也可以是别的。
一些词汇在夸大它们的力量(小昕从日本订购了一种盐,粉色的)。
我们的语言,出现某种力(你就当我疯了吧)。
我喜欢原罪这个词,这没什么。
站起身,一样的及膝长靴。
露着大腿在杭州街头。
小昕在前面走的时候我连去哪都懒得问。跟着就是了。
除了能够进入,我们还需要结界。
这算什么小说呢?我问小昕。
你知道不知道赛博朋克?
小昕反问我。
你那篇星巴克扮鬼事件跟赛博朋克有点像。
我一脸茫然。
(好在银翼杀手就要上映了。我并不太清楚其中的关系,不过我可以去了解。)
我更喜欢小昕的地下世界以及小昕的失踪。
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星巴克的失踪。以及摄入了肉桂粉的癫狂。
实实在在的癫狂。
脱离了社会性的,实实在在的沉甸甸的疯。
我和我的疯,离得太远了。
我们开了一辆黑色的大众。我们穿过隧道。我们约过一座座油漆般绿的山,我们到达底处。
底处,也就是藏的最深的位置。
肉桂粉藏在星巴克的台子上,它含有的密码和雪地小屋里的一样多。
那里是记忆的封存之处。
一切以另一种意象出现的时候,它是安全的(有小孩的哭声)。
好吧我以后在这种故事里设定一个科幻元素。
以后这种故事就叫科幻小说吧。
新小说,科幻小说,不错。世界对我的吸引力,不过是坐在星巴克,拿起一瓶肉桂粉那么多。
跳起了舞,跳起了舞,跳起了舞。
小小微光,伴我闪亮。小小微光,伴我闪亮。小小微光,伴我闪亮。
星巴克所有的人,先抬左脚,再抬右脚,摆动胯部,前后转圈圈。
IT男把手搭在前面的家庭妇女肩上。家庭妇女把手搭在谈生意的创始人肩上。创始人把手搭在游戏公司CEO肩上。CEO把手搭在拿了一杯奶茶蹭坐的外地人肩上。外地人把手搭在进来上厕所的发传单的年轻人肩上。年轻人把手搭在少白头的店员肩上。
先抬左脚,再抬右脚,摆动胯部,前后转圈圈。
啪嗒,啪嗒,Duang。跳。
咔哒,咔哒,小昕的肉色兔子翻跟头。
滋滋滋滋,门廊上的灯发出声音。
汇入。
(未完待续)
2018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