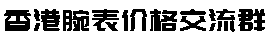
2022-05-07 14:09:50
我早想写一段文字来记述那已经过去的三百多个日夜,但却一直不敢动笔,因为要写的实在太多,还不包括不想写但必须记住的东西。正巧,《夕秀》第四期即将出版,主编来催稿,还要大部头的。于是,几个晚上便诞生了下面的文字。此时,我才发现过去的故事竟象一串断了线的珠子,再也串不起来,只好拾一两颗,暂且珍藏吧。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入乡随俗”。客居他乡,整整一年,方知此四字的含意,那就从一年前的小屋说起吧。
1987年12月19日
我的小屋
我是个爱做梦的人,而且做的梦都很美。
小时候,我梦见自己拥有一个世界,那里面只有一座山,山顶上是一个大湖,我经常独自架着一只纸船在上面漂。湖中心好像还有座山,山顶上好像还有个湖……
后来,我梦中的世界换成了一间小屋。屋里决不是什么富丽堂皇,只有一张书桌,一把椅子,还有个书柜。别小看它,对我来说,这足够了。我可以在里面随心所欲。在这里阳光和月光是等价的,墙壁上挂满了欢乐,为什么不呢?这是我的天地呀!
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因为梦外的事实告诉我再小的世界也不会只有一个人。
这也是一间小屋,只有十二平方米,住了七个人,从窗子到门刚好七步,非常准确,因为我已试测过无数次。
七个人来自七个地方,天南海北,每人说一句,也有七句话。韩信的同乡,谈起漂母潭来津津乐道;生长在荆州古地的人,埋怨当年诸葛亮就赖在那儿不走;还有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他说一家人都平安,连我们也为他庆幸。
几个月以后,别说父母兄弟,就连别人的亲戚朋友在哪儿,长沙有什么熟人也都了加指掌,于是似乎真正做到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别的屋谈论的问题我们屋也谈论,什么孔老二与猪八戒,,王老师和教导员,×××与×××,谈到神秘处,彼此悠然心会,永恒的话题的确永恒,妙处难与君说。
别的屋具有的现象,我们屋也一定有。见对门过生日真热闹,弟兄们也盼来盼去,好容易某君快到生日了,两星期前就已商量妥当。逢年过节,玩个通宵达旦。周末也充分利用,不熄灯,不上床。
也许就是因为热闹的时间太多,寂静对我来说,便是极其珍贵的。
我的床靠窗户,很容易领略到窗外的风景。由于是一楼,又是朝阴的,因而能看到的天地实在有限。不过,妙就妙在,这有限的天地竟能包罗几个有趣的景观。近处,可以称得上是个小废品站,赤红的土地上洒满了一块块的白米饭和不大不小的罐头盒、废纸,应有尽有。一条清晰的小路分开了另一个世界。那边的青草十分茂盛,四季如荫,交错分布着几棵叫不出名的树。树干不很粗,但却十分高,究竟有多高,反正在屋里是望不到头。树后夹杂着灌木丛,草也很高,密密麻麻,不知深浅。那里很少有阳光,但我知道那是绿色的王国。不骗你,这景色已经有些野外的味道了,只是一堵高大的围墙和几间低矮的平房影响了你的想象。
当然不只这些。清晨,总是鸟儿的世界。尤其在夏天,太阳早,它们也早。几次都把我从床上叫起来。细细数来,有七八只,象是老主顾,从这颗树跳到那棵树,好不开心。它们经常跑到窗前,来饱餐一顿不花钱的饭莱。它们是那么悠闲,在窗前漫步从不恐惧。有一种鸟,很大,是黑色的,尾部有很多花班,十分美丽,叫声也很诱人。我们几次商量要抓一只回来,但终没有去,于心不忍。
与鸟儿共进美餐的还有老鼠。在我的印象里,老鼠总是一副瘦骨嶙峋、油滑可憎的面目,但却从没有见到过窗前这么肥硕可爱的形象。一只老鼠,足有几斤重,怪不得人说科大“人瘦鼠肥”。它们不象鸟儿成群结队,而经常是独来独往。它们在窗前徘徊着,咬几口饭,又警惕地左顾右盼。吃饱了,又刁起一团米饭,晃着滚圆的屁股,一蹦一蹦地越过小路,消失在密草丛中。每当这会儿,我总要说声一句,“再见,可爱的小家伙”。到了冬天,它们活动十分频繁,每天都要在这片土地上出没,而饭莱也事先准备好了。它们好像也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不客气。我们有意吓唬它们,它们也置之不理。有一次,我读书累了,抬头看到窗外草丛上蹲着一只大老鼠,正朝我呲牙咧嘴。我看着它,笑了,它却转身跑了。
旁晚,夕阳不仅把天边映红,也把这片野地装点一番。红色的墙,红色的树,红色的落叶,红色的土地。草木都好像很不情愿,望着快落山的太阳一动不动。而这时,我总想对它们说:太傻了,还有明天呢。
至于什么“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树影婆娑,珊珊可爱”的夜景,想必也是有的,只是我未尝注意。倒是曾经有野猫的叫声,让我难眠,象婴儿的啼哭,却十分凄惨。有一次,我忍不住,从窗口望去,见房上蹲着两只,架式很威武,看不清颜色,只有两只眼睛闪着光。我望了许久,直到它们离去。
别看这里有猫有鼠,但十分和谐,鸟兽之间也和平共处,从未发生过争战。也许这就是我喜欢窗外的原因之一吧。
有时,老鼠也进屋,到处跑。据说八三级有一男生早晨起来,发现枕头上爬着一只小老鼠,睡得正香,方才大惊,竟与老鼠同床共枕了一夜。
其实这算好的,幸亏不是蚊子。这儿的蚊子实在厉害,稍不注意就会红包四起。蚊帐一直要挂到冬天。若没蚊帐,就跟下地狱差不多。就是有,每天也要折腾一会儿,打着手电围追堵截。若是有个落网的,这晚上就别想睡好。这可是件头疼的事。有时候,自以为坚壁清野,可以高枕无忧了,哪知道半夜不知从何处又蹿进来几只。后来,我索性不管它,让它吃饱,第二天早起再抓。装着一肚子的血,蚊子的灵敏性很差,一抓一个准,只是要流点儿血。经过几次激战,我长了不少经验,也领教了蚊子的厉害。我曾凑了四句打油诗,专道此景:
空作堂堂男子汉,区区无奈小虫顽。
几番夜半闻声起,血染帐纱点点斑。
虽然粗陋了点,但却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同屋的吕德宏说:“长沙的蚊子真不要脸,我们锦州的蚊子从不咬人”。我险些笑出了眼泪。我忽然明白了我为什么对老鼠的印象比蚊子好得多,就因为老鼠从没有侵犯过我的利益。
科大还有一宝就是辣椒。原来总认为四川人吃辣子很凶,没想到湖南人更甚。陈建文顿顿吃辣椒,我可没那福气。有一次,一狠心吞下去一大块,害得我绕着操场跑了三圈。不过时间长了,倒也锻炼出来了,每顿不吃反倒觉得不可口。那天偶然看报,竟发观湖南省的旅游标志是一朵芙蓉(湖南被称为芙蓉国)和两只辣椒。不伦不类,真让我哭笑不得。
吃辣椒又据说是为了防止瘴气。长沙确实很潮湿,阴多晴少,有时真可谓阴雨霏霏,连月不开。在北京时就听说,这儿的东西一个月不见太阳,就会长白毛。那天,妈妈来信催我把床上的东西拿出去晒一下,我屈指一算,糟糕,已经有两个月了,连忙拿起被褥就往外跑。可到了门口,又退了回来,外面正下着小雨。
并不是什么事都能让人发笑,尽管我很爱笑,但免不了也有生气的时候。我靠着窗,地理位置在屋里是最好的,但却离贼近了。先是桌上刚买的菜票不翼而飞,后来早晨醒来,手表也不见了。报知教导员,他也没办法,只好再买一块。他们能偷,我们能买,仅此而已。桌上不再放可偷的东西,然而床上的毛巾被和衣服也陆续长了腿。好在窗户内还有铁栏杆,否则连被子、枕头也难逃劫难,甚至连床都可能被掠走。每天打埋伏,也不一定抓得住。只好把蚊帐放下来,让窗外的“君子”看不到床上的东西。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小偷也是高等动物,他会在窗户外面,拿竹竿挑开蚊帐。幸亏一位同窗回来及时,小偷跑了,竹竿依然立在窗前。我看到这情形,气得想:这也太放肆了!我真想用这竹竿砸他的脑袋。后来,有人告诉我,研究生楼抓住两个小偷,让我去看看。我咬牙说,一定去,但之后竟也忘了。好在,挨过几天,我们就要搬到三楼,从此就不用提心吊胆了。
小屋里喜忧各半,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人高兴,有人苦恼。小屋是纯洁的,而小屋的主人呢?
每当有人说我们屋乱的时候,我总会指着墙上的“何陋之有”的墨迹让他们看。不过,我并不敢自比君子,有时候倒觉得作个小人也行。其实小人也很难当。察己则可以知人,所以我早就想把那幅字摘下来,永不再挂。
快放假了,全队都要搬到三楼,屋里有人对我说他要搬到别的屋去。我虽然理解,但还是吃惊。其实,在我第一次发现屋里的笑声不再自然的时候,就应该料到会有今天。“楼上虽然视野开阔,但风很大,还是住阳面好”,有人如是说。我沉默了。
我最后一次见小屋是离开长沙的那一天。满屋狼藉,已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我只是在窗前站了一会儿,一只老鼠蹦跳着,就在我眼前。我叹了口气,想到,我们刚来时出生的小鼠,现在也有一岁了,想必也是圆滚滚的可爱的形象。我把我那块不见阳光不出字的电子表,挂在了窗钩上,转身走了。
开学了,已搬到三楼后的第一天,我推开窗,才发现,少了树,少了鸟,少了那一片绿色。
文 山 会 海
不知从何时起,我身上一下子多了许多头衔。接着便是一大堆公文、会议,还有乱七八糟的杂事。起初我的热情很高,甚至可以说是“斗志昂扬”。宿舍成了会客室,人来人往,门庭若市。要么是系里各部的通知需要传达,要么就是外系来人联系文艺活动的事宜。经常是系学生会主席前脚刚走,后脚就进来团总支书记。再加上文坛上的一些新朋好友,各刊物的头头脑脑,一天到晚忙于应付,有时晚上熄灯后刚睡下,又被叫起来。我几乎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毫不夸张),更别提读书本写作业了。到最后,我都不敢在宿舍里停留,除了晚上睡一觉。
上学期我有一半时间是在队部里度过的。每当走进那间十八平方米的屋子时,我总要想起世界名城日内瓦。《半月谈》的总编曾告诉我在日内瓦每年要开上千次的国际会议,大到美苏首脑会谈、国际裁军、经济发展,小到探讨澳大利亚袋鼠的繁殖能力--名副其实的会议城。而我们队部也不逊色,团总支、班委会,还有党支部好象按照日期循环,很有规律,白天开不完,熄灯后接着开,多到十几人,少到三两个,内容丰富多采,涉及到全队学习、生活的各个角落。开过半夜,已经不足为怪。有一次干部们开到夜里两点钟,其中一项议题就是督促同学们早睡觉。别笑,这是真的。
我在系里队里都是搞宣传的。自然,一些笔头上的事情便落到我身上。我也想,既在其职,岂敢不谋其政?于是起早贪黑,吃饭都拿着一杆笔。整理会议记录、评审各种材料、拟定活动计划、抄写各项通知等等,甚至连队干部的讲话稿都由我来起草。同时,还要撰写一些文章,主编两个刊物,可恨每天只有二十四小时。没办法,只好少睡─点儿了。本来一百多人的队,事情就不少了,偏偏本队又是学校的典型,各方面都很出色,上交的材料也就自然要多一些。我记得我们经常几个人组成一个班子,抄写复印各种材料,有时催得紧,夜以继日地干。审稿、润色、组织等等一系列环节,都必须保证质量。幸亏队里人才济济,才能顺利完成。可没过几天又下新的任务。当然,队干部也是自始至终和我们一起战斗。结果很理想,我们最终被评为三好队,可谓当之无愧了。
陈建文说我是华威先生。我觉得这比喻再恰当不过了。我参加各种会议或活动,一半是出于应付,一半是出于虚荣。
我的最高记录是曾在一天内参加了四个会议,共花时间七个小时。至于在过去的一年里经我的笔写下的文字,大概已有十几万字了吧。
爱情的故事
国防科大不准谈恋爱。这是每一个新生刚入学便从队长、教导员那长篇训词中领悟出的几个真谛之一。据说这还是当年元帅来校时下的命令。然而据我所知,任何一对相恋的或尚处于蒙胧状态的男女,都未把此事放在应有的位置上。这使我时常想起英国诗人狄金森的诗《爱,先于生命》:
爱,先于生命 ──
后于,死亡 ──
是创造的起点 ──
世界的原型 ──
本来嘛,爱情到了八十年代,早已超出了两人的范围。情侣们形影不离、朝夕相处,这曾被历代诗人歌咏的景象是最人性的象征。它能遍及世界的任何角落。凡是有鲜花开放的地方,凡是有明月朗照的地方,凡是有歌声飘荡的地方,就会有爱情在释放,在燃烧,谁能禁止得住?让那些严厉的队干部们在入夏的夜晚,到体育场的看台上去转上一圈,真不知他们会有何感想。
几个月前,某系举行辩论会,正反两方辩论大学生谈恋爱,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结果正方赢了,颇鼓舞人心,掌声就是最好的论据。有一位热恋的朋友对我说,他很轻松,每个月的钱两人一起花,洗衣服女生都包了,繁重的作业也有人分担,遇伤心的事彼此也可安慰。这样的美事,何乐而不为?说得我都动了心,就象孙大圣在花果山上,听得太上老君对天宫仙境的一番渲染之后,大喜道:“俺老孙就跟你走一遭”。说罢,一个筋斗云便去得无影无踪。
然而,玩笑归玩笑。虽然科大不乏成双成对的人,但这华竟是少数,更多的是处于一种“激发态”。男女彼此保持着距离,举手投足颇有讲究,你不来我也不往。据一位同窗的分析,如果今天一兴奋,见面时打一次招呼而未被理睬,那么明天再见,即使离得再近也绝不先开口;如果这次多看了你一眼,那么明天一定少看成干脆不看,以求心理的平衡。谁若是打破了这种平衡,便会招来议论,也许自己并不太知道。
人说女孩子都很敏感,但我觉得事实并非如此,有的男孩子也很敏感,不是对自己,而是对别人,有时甚至是神经过敏。某某先生与某某小姐多说了几句话或交换了什么东西,便会引来很多惊奇的目光或带着神秘的问话,叫人摸不着头脑。问之何故,还振振有词。既然已是耳闻目见,便可臆断其有无了。无奈。
谁都知道,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见钟钟情几乎没有,就是两厢情愿也只是几经波折之后的事。然而有些言语,有些举动,确实会让有心人面红心跳。也许是一个秋波,竟也是那么难忘,以至于几年之后还会浮现在跟前。这算幸运的,因为毕竟是个美好的回忆。相反,如果总是一个人苦恼,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或许是一次巧遇后竟展转反侧、夜不能眠,就象《橄榄》主编李舟军写的一句诗:“也许我们望穿秋水,在水一方却无伊人的芳迹”。也或许是送了舒婷的《致橡树》却无回音。说实话,我很佩服他(她)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谁敢去试那“展不开的眉头,挨不完的更漏”?但是生活往往是这样的,丘比特拿着箭就是不放,你有什么办法?总想着“灯火阑珊”或者傲然独处,水火不容,会贻误良机的。而且错过的,永远不会再来。
至于在科大公开的追男逐女,我只是有所耳闻,从没亲眼见过。
一个已经毕业的朋友对我说,他班上的几对没有一对成的。我并没有做过追踪调查,但我相信他的话。天宫也并非十分如意,连孙猴子最后不也反出了南天门,逃回花果山去了吗?
除了恋者、怨者、恨者,余下的便是沉默。也许这就是理智。
泰戈尔说:“如果在爱中只有痛苦,那为什么还要爱呢?”
是啊,我也问:为什么?
有一天,一个朋友忽然对我说,他在长沙某书店见到了一位很有气质的女孩,冰清玉洁,温文尔雅,筒直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很想再见她,可又不知她在何方。他无法解脱,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很简单,以后少去逛书店就是了。
去年。我过生日时,一位高中的同窗寄来一张生日卡。上面写着:“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我笑了,这不是夸我,这是在咒我。我忙回信说:你真是“过奖”,我可不当史湘云,不希望将来的命运会象她那么惨。我还不到二十岁,以后的事说不清。也许我也同样会爱得如痴如醉,爱得神魂颠倒,也同样会说:“我不明白,你我相爱之前在干什么?”很有可能。
我曾看过一部小说,上面描写两个美丽的姑娘,同在大学读书,是知心朋友。她们经常在一起讽刺班上最有风度的男生,而且还比看谁骂得最狠。好象越这样,自己就越清白越高尚。但是背地里,有男生向她们献殷勤,嘴上不说,心里却是很甜美的。她们还相约谁也不准谈恋爱。结果,其中─人背约,竟为此丧了命。
唉,爱情实在太微妙了,谁能预知自己的归宿在何处呢?
佛语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倒觉得,假如当初不系,也就用不着解了。
在这方面,我很欣赏台湾作家三毛的话:“爱情有如佛家的禅,不可说,不可说,一说便是错”。
纸上的世界
远离故土,客居他乡,书信总是免不了的,况且这还是大学生话的重要组成部分。
刚入学的新生,信件往来颇为频繁。同学中总是以收信之多为荣。我有一个室友是全队得信最多的,他创过一天连收九封信的记录。我也创过记录,是写信字数最多,一天内写了六封信,封封都在千字以上。
时间长了,信也少了,这时来信的才是真正的朋友。
的确,收到一封信无疑是件快事。这不仅会得到同屋人的羡慕,而且更重要的是慰藉自己那颗过于急切的心。然而我却不愿收信,并不是我没有朋友,也不是我过于清高,而是因为我不想回忆过去。我很想把自己置于世外桃源之中,尽管我也知道这办不到。所以我的信一向不多。
我的中学生活是美好的,我相信别人也是如此,但恰恰因为美好,我才不愿回忆。
在我的信里很少谈学习或生活,多半是写怎么游玩,什么韶山红叶、岳麓秋枫、桔子洲头看万山红遍。我写起来绘声绘色,只是游洞庭湖时略微扫兴,竟没能住上─夜,独驾一叶扁舟,像古人那样“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不过,这些描述也足以让读者倾心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然而,我觉得我是在掩饰,到底掩饰什么我也说不清,
老朋友、老同学们都知道我很爱游山玩水,自然信里也少不了这些,我也让他们多谈些风景。然而那天收到一封在杭州上学的老同学的信,让我改变了观点。她说刚骑车去游过绍兴,绍兴给她的印象很好,“到处是水、桥,典型的水乡风味……游了东湖、兰亭,美得很。鲁迅故居、百草园与三味书屋,沈园大通学堂。还跑到咸亨酒店去喝老酒,吃茴香豆,学做孔乙己,结果搞得脸红脖子粗,不敢见人”。她们还跑到灵山,又去游金华的岩洞,一山三洞,奇特无比,感觉各不相同,并邀我有机会一定去玩。读罢,我竟下决心以后再也不写游玩之事了。
有一位低年级的朋友来信说,他已读高三了,可一点紧迫感都没有,虽然美院的教授已点名要他(因为他的画在全国得过奖),但他却想毕业后去做生意,因为现在“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还有几位在外地上大学的同学来信诉苦,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我回信总是劝说,可那些话我都不满意。
在京的朋友来信最勤而且最长,字里行间洋溢着阵阵春风,不是叙述回母校的所见所闻,或者大学校园里的奇闻怪录,就是描绘又如何重游香山和北海,去瞻仰当年我们一起为了记录友谊而做下的永久象征。唉,他们总让我失望,而且生气。
除了这少许的几页信纸可说些废话以外,还有一个更开放的世界,那是日记本。
在这里,可以说人人都有日记本。因为它太重要,少了它也许就没有了朋友。有个女生曾对我说,她总是把眼泪往日记里流,我很是同情。
我不想写信,但很喜欢记日记,尽管我很懒,总是松─阵紧一阵。那天偶然翻了翻以前的日记,发现我竟会用那么多篇幅描写梦境,也许我做过的梦很值得写。
与书信相比,日记里要现实得多,现实得让人看了伤心(并非仅指我)。翻开过去的日记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痛苦。我有一个朋友每写一篇,就撕下来烧掉,因为他受不了。
于是,我敢说每一个精致的小本便是一部催人泪下的历史。
我有时也凑些诗在日记里,或者些生硬的语言。然而过后竟发现那里面充满了哲理。我于是以此自我陶醉,竟真觉得自己似乎可以做个哲学家。
我随便翻了一本日记的最后一页,是这样写的:
一下午我睡了很久,晚上可不能荒废了。我去听音室,碰到了舟军,他笑我这么晚才来……
他说他又写了一首诗。我笑了,因为他曾经告诉我以后再也不写了。他给我念诗,最后两句是:
“我不知如何走进你的梦境,
只好把白云的邮票贴满天空。”
我笑了:“这又是借鉴谁的?”
他说是他自创。的确写得不错。
分手后。我叹了口气:
梦境是永远不会到来的,
我并不期待。
我只期待明天,
因为只有明天才从不违约地到来!
我忽然发现,我的世界竟是这么宽广,可惜仅仅存在于纸上。
闲心与忧郁
主编《夕秀》,使我结识了许多科大文坛上的朋友。在这之前我竟然不知科大还有这般丰富多彩的世界。于是,也便有了闲心。于是,“宿舍─食堂─寝室”这原本单调的三步曲被这闲心抹杀得一干二净。
在认识吕建军以前,我对中国的新诗是不屑一顾的,也是一窍不通的,尽管有时也写一两首。他向我推荐了几首新诗。之后,我竟发现《朦胧诗选》里也有我所憧憬和追求的东西。
我们俩的处境很相象,他办《月亮岛》,我主编《夕秀》;他编排《研究生通讯》,我又去搞《银河星》。
他经常带我出入电影院、舞场、校外的小吃店,甚至新华楼。之后,又认识了几位朋友,都道相见恨晚。今天你请客,明天便是我作东。为一件事能聊上几个小时,不知为何有这许多话,而且多半是废话。这使我想起了《易经》里说的:“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看来我们都作不了吉人。
每每在舞池边上碰到他们,于是“缕缕薄烟也便辜负了彩灯馨香的召唤”,只讨论下次请客在哪。
德雅村有个馄炖店,很干净,第一次建军带我去时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此这里又多了一个无聊的常客。因为我们并不是为吃而来的,但到底为什么而来我也说不清。
噢,这就是闲心吧。
我一直觉得我很快活,直到六月的一天晚上。
在那个馄炖店里我遇到了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桌上还放着半瓶白酒。他自称是某系八五级的。他说认识我,我很是吃惊,因为这不象醉话。我问他为何要这样,他反问我:“你喜欢古文,可知道《世说新语》里有一个殷中军?”
“是那个终日恒书空作字,咄咄怪事的殷浩?”我有些不快。
“对,……”。他打了个饱咯,喷出满嘴酒气。
“那,这又有何干?”
“上人著百尺楼上,儋梯而去……”
“噢,我明白了。”
我不禁顿生敬意,抓起桌上的酒瓶,为他满上─杯,也为我满上一杯。我们相视一笑,然后一口把酒喝干。
在走出那个小店以前,我还以为我好象从来没有过忧郁。
看晚霞
小对侯,我最喜爱干两件事,数星星和看晚霞。长大后,渐渐发现已经没有几颗星星可数了,那只不过是个童年的象征。然而看晚霞我却从未放弃过。
我还曾记得,上中学时与一位同学朋友相约天天傍晚去看那落日余辉,相互寄托思念。她在郊区上学,看晚霞是很容易的,可苦了我,站在窗前或阳台上,通过楼群的缝隙,只能看到西山那隐隐约约的峰峦,而且还必须是晴天。即使这样,我还是不放过每一次机会,直到万家灯火。想必太阳也能记住我了。平时,晚霞就是西山背后的一张用朱笔涂抹得很不均匀的红布,却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和谐。而夏季傍晚,尤其是大雨过后的万里霞光,则是十分艳丽的,润红润红的绸带挂满了天空,清新淡雅,叫人见了有说不出的畅快,可算是北京最美的自然景观了。
然而那一切与这里的傍晚相比,便要逊色得多。
长沙没有北京那么多高楼大厦,用不着你刻意去登高,便能大饱眼福。有时甚至走在小道上,一抬眼,那天边的落日正冲着你微笑。
时常是远处树梢先笼起一层薄薄的烟雾,之后便是沸腾了一天的太阳失去了耀眼的光芒,越发的红,越发的圆,好象是被谁有意地挂在那里。烟散了,西边的天开始变红,裸露的山峦被落日烘出庄严的色彩。这时,那几缕浮云便被吸引过来,舞弄出千姿百态,挥洒着自然的风采,那轮落日渐渐隐没在这薄薄的霞层里。至此,一切自然的神韵,一切奇丽的天工,都归了天边那一抹晚霞。
不过,有时在这里只能看到孤单单的落日,没有云,没有霞,但也是极精彩的。或者是红日斜晖下教学楼畔的几丝碧绿叫人惆怅。更甚的是那条贯穿南北的铁道上时而传来阵阵轰鸣,冲破白雾,回荡在空荡的校园里。于是桥上、楼上的异客又平添了一段乡愁。这是落日的罪过,我不怪晚霞。
使我最难忘的是去年秋天的一个傍晚,那时我站在系大楼的顶楼上,无意间放眼四周。谁知这一望竟摄去了我的魂魄。周围没有高楼,毫无遮拦,可以一眼望到西边连绵起伏的岳麓诸峰以及那下面一条银白色的链带──北去的湘江。其实四周都是山。一轮红日架在麓峰的山腰上,红红的、圆圆的。这是我看过的最美的落日。我朝东望,见性急的月亮已挂在天边,很白,也很圆,只是淡淡的被浮云衬托着。这时西山背后忽然涌出层层云雾,飘忽不定。唐人的诗句“一聚一散天边霞”道得最为贴切。太阳仿佛也激动了,竟也放出了光彩,照耀着升腾的云霞,肃穆的群山,还有赤红的土,碧绿的树。晚霞越聚越浓,层层起伏,欲将楚天渲染,竟不顾群山的阻隔,落日的呼唤,奔腾出来,扩向远方,把红色的绒幕挂满了天边。壮哉此景!我不禁大发诗性,不修格律,随意即景,倒真的凄成了几句:
适暮登高楼,南国万里空。
麓峰承火岳,湘水下荒洪。
碧树残烟阔,白月落日红。
莫道桑榆晚,余晖色正浓。
这是我看到的最美的晚霞。
我又想起我那位朋友曾向我介绍过一部小说《当晚霞落山的时候》,其中男女主人公几经磨难,几经挫折,十年后竟又在泰山重逢,道尽所有的辛酸,冰释所有的误解,最后一道去看晚霞。多么富有诗意啊。我的朋友曾写了一本《晚霞日记》,可我却只字未写,只把它记在心里。因为,每当自然将你陶醉的时候,语言和文字便显得那么无用。
如果说朝阳是给人以希望的话,那么晚霞便是给人的安慰。我总是这么想。
朋友,如果你感到孤独,感到寂寞,感到伤心,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那就让我们一起去看晚霞吧。我也有好久没去看它了。
写在后面的话
刚写完这六篇印象记,我总觉得似乎少了点什么,忽然想起一年级期末曾经写过一首格律诗,满纸的高调子。当时写它就是为了留作以后回忆时的参考。我本想把它登在这几篇小记之后。可前几天翻了翻废纸稿,竟没有找到,很是遗憾。昨天一位朋友问我:
“你是写自然的吗?”
“当然”,我很肯定地回答。
这么一想,还是丢了好。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相关推荐
友情链接
Copyright © 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香港腕表价格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