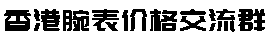透过北角咖啡馆的玻璃门向外望去,我看到了康妮。
二十年前,康妮和我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同学。当时联合利华公司提供五个实习机会,她和我都被选中了。特别之处是三个月后,表现最好的学生会获得奖金,金额相当于MBA项目学费,是一笔令人瞠目的巨款了。
策划将多芬和立顿品牌全面植入《丑女无敌》的那几位,当时应该还没加入联合利华市场部,否则她们不会错过绝好的打造职场真人秀的机会。摄影组将全程跟踪每个学生,记录我们如何努力学习,如何加班赶进度,如何犯错误挨训斥,如何在背后吐槽老板。部门经理们时不时现身,发表些毒舌评论。同事们也有机会穿插分享办公室八卦。
遗憾的是,这些统统没发生。甚至连获胜者揭晓也只是通过电子邮件,完全没形成高潮时刻,甚至可以说是反高潮。粉丝投票哪里去了?评委密室讨论哪里去了?悬念解开前插播广告哪里去了?主持人一口气念出几十个赞助商名字哪里去了?
康妮获奖是实至名归,我心服口服。智者自有智慧的规划和选择。毕业时她拿到了知名咨询公司的聘书,让我羡慕到心痒痒的。然后她轻轻推开了这个机会,让我惊讶到牙酸酸的。在制药企业备受重用时,康妮又辞职当起了全职主妇,让我莫名到嘴歪歪的。
康妮及全家逡巡世界各地多年后,现在定居中国香港。她容貌变化甚少,身姿依旧矫健,照顾三个孩子的起居和学业之余,自我充电不懈,学习、健身、公益日程排满。时隔四年再和她见面,我们像是捡起上次中断的谈话,很自然也很亲切。
我们谈以前学校里的事,有些尚清晰,有些已模糊。我们谈同学们的近况,有些可预料,有些想不到。我们更多谈的,是香港近年来的种种变化。康妮在此居住多年后的认识,自然和生活在上海的我不一样。但毋庸置疑,香港的黄金年代已经过去了。
随着制造业内迁,优渥的蓝领工作在香港消失了,中产阶级日益拮据,贫富差距更大。很有可能,将来香港能提供的,只有少数高薪高技能工作——就像康妮的先生所在的投资银行,以及必须在当地的的低薪服务工作——就像正在给我们倒咖啡的侍应生。不过前者面临全球化残酷竞争,而后者则很难提供向上的社会通道。
我很想知道,明天的上海会不会就是今天的香港?如果要避免跌入这种陷阱,又该做些什么?不是一杯咖啡的时间里能说清楚的。
在铜锣湾吃重庆火锅,是汶浚的提议。
汶浚曾是我上司。那时他年纪尚轻,被美国高露洁公司派到江苏扬州新收购的民营企业,全面负责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我MBA学位拿没多久,专业技能欠缺,唯有一腔热情。汶浚聘请我担任培训经理,全无保留地传授知识和经验,有赖他的帮助,我成长很快。
扬州当时尚不发达,一群天南地北的员工平时无甚去处无甚消遣,日日一同上班一同下班,然后结伙聚餐、打牌、休闲。我是在晨间班车上得知九一一世贸双塔倒塌的消息的。那种亲密的同事和伙伴情谊,在我因家庭原因离开时戛然而止。回想起来,这是唯一我辞职时因舍不得而伤感的工作。
汶浚后来也离开了,曾短暂来上海发展,接着返回故乡广州,陆续在不同的外资企业工作,都是在人力资源部门。结婚之后,他移民来香港定居。或许是语言相通的关系,看起来他融入得非常好。
汶浚如今脸形削瘦,全不似当年肥肥的样子,体脂含量看起来很低,变身程度赶得上杜海涛。果然,他自述多年坚持运动,刚刚去东京跑了马拉松,近来又迷上了踩单车。
我们谈起当年的同事们,更多是谈如今香港的工作场所。香港人的勤奋程度和专业精神依然值得赞许,但当初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带来的优势,如今随着科技革命而荡然无存。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亚太区管理功能从香港搬迁去上海或者新加坡,或者干脆将亚太区拆分成若干个独立业务单位。这些都收窄了留在本地发展的香港人的职业通道。
汶浚如今负责管理亚太区的人力资源部门,一半时间要四处出差,吃火锅前刚从新加坡飞回来。他谈到日本人做事很谨慎,过分看重既定规则,然后又意识到,在他部门工作的香港人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自己的过往经验与之完全吻合。
十多年前,我在复旦大学做校园招聘宣讲时,有人提问:“请问作为跨国公司,飞利浦对香港来的学生有没有特殊优待?”我当时回答:“飞利浦致力成为公平雇主,不歧视任何地方来的学生,包括香港”。众人热烈鼓掌,提问的学生觉得有点失望。换成今天,他应该对这个答案很满意才对。
丹在赤柱广场前朝我招手,我还不敢相认。他脸庞圆润,长发及肩,黑框眼镜,说是高晓松倒有三分相像。
我记忆里的丹个子小小很瘦弱,但毕竟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三十年前了。我们是初中同学,住得不远,每天乘公交上学都一路聊天。丹比我小整整两岁,因为他是个神童。
我上初三时,神童丹在尖子班学习。我上高中时,尖子丹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霸。我上大学时,学霸丹在英国剑桥大学读博士研究概率论。我到上海时,博士丹踏进金融界做对冲基金了。英国美国新加坡一路走来,如今丹住在香港。按他的说法,“这里税低”。
当年我们坐在教室前的花坛上,聊苏联改革和叶利钦,如今我们坐在美利楼的海鲜餐厅,聊中国经济和川普。丹的智商依旧抛我几十条大街,看法非常尖锐和透彻。我更多是倾听。
有个念头闪过我脑海,康妮、汶浚和丹都提到,他们是租房子住的。如果投资银行家、企业高管和基金经理都不买房子,是不是说明香港的地产市场有了严重的偏差?是不是说明有待成功的年轻人置业前景渺茫?是不是要引用流行语说“房价限制了香港人的想象力”?香港还有希望吗?
应当是有,康妮、汶浚和丹都有生根长期发展的打算。
同样对香港有信心的是同学刘芹。这回没见到他,只收到微信“抱歉还在北京处理工作,周末也回不去香港了”。我一点不觉得意外,著名风险投资人忙才是常态。
刘芹在采访里谈到,在投资小米前曾和雷军通电话,从晚上九点一直讲到早上九点,新的一天开始了,这句双关语用得极妙。投资眼光如此卓著的刘芹,选择定居香港,肯定看到了我们忽略的东西。
以作者的身份,我从文化方面也要给香港投一票。前一晚,我在中环欣赏喜剧表演,暖场的是美国白人男性老师,担纲的是英国来的裔女性,观众里有爱尔兰学生、新加坡医生、罗马尼亚银行职员,电脑工程师等等。这样的交融局面,全世界只有少数城市才会有。
我有种感觉,东方之珠仍将在我们身边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