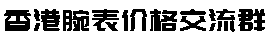姥娘家村有一种像燕子一样的石头,叫“石燕”,是非常独有的、稀缺的玩意儿,姥娘经常跟我说起,而且说她曾经见过。现在看应该是一种原始鸟类动物的化石,《保德州志》里有记载。出于好奇,我一直想亲眼见识,就随便问问。姥娘为这随便一问,就一直找,最终没能给我找到那种神奇的“石燕”,也就是这样一件小事都能让老人家觉得特别遗憾。姥娘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去实现我所有的愿望,满足我所有的要求,老人家就是这样简单,要设法赢取所有邻里族内、亲戚家人的满意……
姥爷去世的时候,我年纪尚小;姥娘去世的时候,我已经长大。当时,我哭了,哭得很厉害,哭到非常失态,现在想起来,还觉得……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知道在说什么,在往哪说,为什么说,但还是要说。
姥娘家村过十五,在保德南乡是最有名的,也是最隆重的:有秧歌、旱船,有打铁花、放焰火,有转花灯、唱大戏,对于当时物质条件、精神生活都极度贫乏的山沟沟里的人来说,那个红火热闹劲、那个喜庆高兴劲就可以想见了!
姥娘家村的秧歌、旱船、花灯之类呈一路纵队排列。出发地在阳圪塄上的大队院内。早上九点左右,大队院内响铁炮三声,然后锣鼓在前,唢呐紧跟,伞头随后,再就是旱船、老王八送闺女等文娱队伍和自发组成的人群。队伍顺阳圪塄走来,狭窄的石铺街道外面就是老高老高的河堑,所以,行进速度很慢,拉得很长。秧歌队的头已经过了河,并从沙墕壑转到了楼坪的戏楼前,尾部还在河的对面,蜿蜒足有二里地。其规模之宏、阵势之大,确实够派头。锣鼓和唢呐配合默契,一气呵成,其曲调是这样的,也顺便记了下来:
‖:5 3 3︱ 2. 3 2. 3 ︱5.5 3 5︱1 —︱5.5 5 5︱
1 5 ︱3. 2 3.6︱5 . 咚︱咚咚 咚咚咚咚︱
咚 . 1︱5. 5 5 5 ︱ 1 5 ︱3. 2 3. 6︱5 . 咚︱
咚咚 咚︱咚咚 咚︱咚咚 咚咚︱咚咚 咚咚︱咚 0:‖
锣鼓队背大鼓是苦力活,这个角色的位置非常稳固,一直是村里一个叫文车的人担任,这人先天脑子有问题,别人拽他一把、踢他一脚,他表面上看很不高兴,但从他的表情里,我们能体会到他更多的是背着鼓,走在锣鼓队前面那种无比的兴奋和洋洋自得。秧歌队到戏楼前的场地上,铁炮再响三通,以壮声威,同时开始转场子。转场子有时跑圆场、有时走八字,这会儿,伞头就开唱了:“铁炮三声响连天,我送那瘟神下河南;各路神明把灵显,来为咱全村保平安;秧歌唱起百家兴,风调雨顺好年景;锣鼓敲来鞭炮鸣,迎来一年好收成……”所有的队伍都要跟着他跑。此仪式之后,其他表演队伍分别亮相表演,然后打通开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