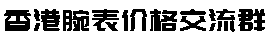“今天的故事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也是一个系列故事之一,人物也是我们周围的人,事情不尽相同,却也相似,不免想起曹雪芹先生的‘假作真时真亦假’,人生就是残酷至极,愿生者能有好的灵魂,愿逝者能够获得安宁。”——阿拉平平
清夜无尘,她痴痴地望着那幽深的天空,云河黯黑汹涌,本来如银的圆月,此刻却有些浑浊不清,像倒映在深井里的玉盘。她盯着月亮里的黑影,听奶奶讲那是广寒宫,里面住着嫦娥和玉兔,一想到寒字,她不禁打了个哆嗦,便回屋和衣躺下,一合眼,便入乱梦。梦境里,她看见母亲温柔地摸着小羊,她又惊喜又害怕,不知道能不能挨挨她,她又看见母亲躺在橡树下,橡子和树叶落了一身,安详又宁静,她大着胆子挨近了她,却满手冰冷,她忙去捡树叶,想让妈妈暖和点,可是冷风把树叶吹得四处飞,戏耍一般,飘啊飘,转呀转,怎么也落不下来。她真急呀,眼泪掉了一串串,可就是够不着,一不留神,绊住了树根……她一惊,猛地起身,两手汗涔涔,半张着嘴,妈妈两个字窝在喉咙里,到底没有出来。
日光翻过山脊,透过墙上的破洞,钻进屋里,在泥墙上留下一个个白色的圆点,亮得晃眼。她微垂眼帘,屋外有风吹过,把她的思绪一寸一寸地扯回记忆深处。那年,樱桃结得格外稠密,又黄嫩欲滴,惹得十里八岭的鸟儿,都来这里偷嘴,她便奉奶奶的命令,坐在树下,望樱桃。奶奶说了,过几天把樱桃卖了换成钱,就带她到集上去玩。她手托两腮,呆呆地望着樱桃,满脑子想着集上金黄发亮的油条、嘎嘣儿脆的方便面、香甜柔软的面包,还有那能香一条街的肉丝面……忽然,枝移影动,光波流转,一位健壮的少年,手执一柄,闯到了樱桃树下,她慌不迭地起身,两手攥着衣角,脸颊通红,一双眸子里全是纷乱的春水。整个世界仿佛睡去,只听风吹过树梢,鸟鸣过碧空……那年,她十三岁。她再也没等到奶奶带她去集上,因为三天后,他用一头跛腿的老驴驮走了她。
他父母早亡,兄弟们早已另立门户,如今是孑然一身,徒留山下两间泥屋。她倒坦然,自己的家境已是那般不堪,这样已经很好了。屋子东面有一条瘦弱的小溪,细微得如一根遗落在大地上的琴弦,她时常去淘菜,偶尔调皮把沙子堆高,看着溪水无可奈何地聚在那里,进退不得。花褪残红,风荷一一举,光景不知流转了多少回,堆沙子的事情儿子做了孙子做,一转眼儿女们都已成家离她远去,唯剩小女儿。小女儿今年14岁,早些年许给了王木匠的大儿子,再过几年就要出嫁,王木匠家是艺人出身,家里一年到头都有做不完的活计,挣钱就跟捡树叶一样,起初,她为女儿能找到这么一个婆家而感到高兴,后来王木匠的大儿子迷上了抽白烟,开始变得十分混账,经常问父母兄弟要钱,要是不给就殴打家人,甚至把自家二弟的胳膊都给打折了。这边,夫妻俩就这么一个女儿,跟宝贝似的,自然不愿意她受这份折磨,便向媒人开口,想退了这门亲,王家人倒也爽快,同意退亲,但是要求退还当初订亲的彩礼五百块钱。这本也无可厚非,但是近几年光景不好,为了给儿子们娶媳妇,他们的生活早已像乞丐的衣服一样,到处都是洞。前年,为了给三儿子娶下媳妇,他们花光了那五百块钱,无奈的丈夫,便又捡起蒙了灰尘的,一头扎进深山,给别人看看林子,打打猎,以挣些零星小钱,慢慢还债。王家本也是厚道之人,从不催逼,但那个混账儿子不知从何处得了这个消息,便隔三差五来闹事,今儿把粮食泼在地上撒尿,明儿往饭锅里丢死老鼠,霸道蛮横地来闹。忽然远处的山道上传来几声嘈杂,把她拉回了现实,她心头一紧,担心是那个混账来了,便慌忙把女儿摇醒。母女俩随便扯了几件衣服,便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向了屋后的乱山林。远处的混球现了她们,开始呼喝着追来了。她又有了身孕,已将近八个月,实在是跑不了多远,她担心女儿跟着她跑不掉,便让她朝另一个方向跑。慢慢地,胸口像压了块千斤重的大石,脑袋被血液冲得胀疼,喉咙紧的难受,肚子也有些惴惴地痛,她便瘫在一棵橡树下,靠着树干大喘气,像一条刚被捞出水的鲫鱼。那个混蛋,跑得脸红脖子粗,到底追上了她。这混球本来黑矮,壮似水缸,因为抽大烟现下却瘦弱得刀把一样。只见他趔趔趄趄抬起枯树枝一样的手,对着她的脸就是一耳刮子,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狗日的婆娘,我让你跑……”那一巴掌把她的面颊打出了几个指头印,原本黄瘦的脸此刻却有了些许红晕,把那个混蛋的眼睛都看红了,他愤愤地吐了她几口唾沫,威胁说:“明日我还来,再不还钱,我把你肚子里的崽儿踹下来。”骂完便悻悻地下山了。她害怕极了,摸摸自己的肚子,里面的家伙安安静静,这账看来是拖不下去了。她开始筹划着怎么还钱,晕晕乎乎的脑袋此时忽然有了一丝清明,她想起去年被九姑妹牵走的驴,驴本是被借去拉石板的,哪知刚拉了几趟,就突然口吐白沫死掉了。当时九姑妹一家承诺给钱,但没过几天,九姑妹的儿媳乌梅,他们家觉得晦气,办了几场极气派的法事,钱花得跟流水一样,她便没忍心开这个口。现下没别的办法,她叹了口气,眼瞅着已近中午,九姑妹家还离这里有几十里山路,她晃晃荡荡地起身,朝小女儿跑的方向唤了几声,无人应答,她不敢耽搁,便拖着疲惫的身体赶路了。一路上,肚子始终隐隐有些惴,她走走歇歇,把太阳走落了,把鸟儿走回窝了,把嗓子走冒烟了,才走到九姑妹家。她表明了来意,九姑妹麻溜起身,给她端了杯热茶,塞到她手心里,眼角堆满了客套的笑,说:“大嫂呀,这钱我肯定给你,只是你把钱给那个烟鬼,,万一王木匠不承认,那可就白瞎了,再说了,那个烟鬼只是吓唬你,你甭害怕,有兄弟们给你撑腰,你怕他个求。”她又哀求了半天,九姑妹只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劝她,但绝口不提还钱的事。几番交锋下来,九姑妹红口白牙,刀切葱似的把她所有的理由都给斩断了。她浑身如坠雪窟,两腿发抖,再缠下去已毫无意义,她心里又牵挂小女儿,便悲愤地转身回家了。一路昏昏沉沉,肚子逐渐痛了起来,她走走揉揉,却越疼越厉害,刀割一般,她暗觉不好,刚斜歪到一块石头上,一股热流便顺着裤子流了下来,她的羊水破了……经历了一个小时的阵痛后,她艰难地产下了一名男婴,又挣扎着起身,用牙咬断了脐带。小婴儿很安静,只浅浅地哭了几声。现下是寒冬腊月,晚上奇冷,婴儿身上的黏液已结了冰霜,她把自己的上衣全部脱下来,小心翼翼地包裹着孩子。她裸露着身体,佝偻着腰,把孩子贴近自己的胸膛,半爬半走地往家赶,走一会儿,她就用脸挨挨挨、用手摸摸小婴儿,起初孩子还别别脸、皱皱眉,但后来越来越不大动了,身体也开始凉了,她害怕极了,一边走,一边朝孩子呵气。今晚的月亮很奇怪,不再银白迷人,很是昏黄暗淡,就像天被烤焦了一个洞。影影绰绰,她看到了自己的屋子,便松了一口气。她唤了几声云儿,屋里并无人应答,看来小女儿还没回来。她把婴儿放到棉被里,赶紧摸索干柴,点起火堆,披上破袄,把孩子抱到火堆边烤。可是孩子的身体太凉了,怎么也烤不热,她含着眼泪,又摸了孩子几下,孩子微微动了下,她心中升起了一丝希望,忽然一股冷冷的细流浇在她的肚皮上,孩子尿了,尿怎么是凉的呢?巨大的悲痛朝她碾压而来,她又大力地扒拉了孩子几下,那个小婴儿微蜷着四肢,紧闭着双眼,小拳头捏得紧紧的,再也不动了……她的灵魂仿佛出了窍,整个人木了,没有思想、没有表情,空壳一般。不知过了多久,她干嚎了一声,手臂死死地钳住婴儿,似乎想要把他勒进自己的肉里。
月亮半死不活地吊在树枝上,霜华的泪水浸满了大地,雾失了魂似的在原野上游荡。第二天,一个手执的男人,在泥屋里哀嚎着。
没多久,男人的亲戚们便把她风风光光下葬了,儿媳们为表孝心,还给她戴了副银手镯,儿子们则给她立了碑,可是刻名字的时候却犯了愁,她没有名字,他们管她叫妈,男人管她叫孩儿的妈,后来他们胡乱给起了个黄草的名字,就这样这个女人在死后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当晚的宴席上,男人们喝得东倒西歪,女人和孩子们吵吵闹闹地看着电影,月亮又把天烧了一个洞,昏黄不清,什么也看不清。
作者简介:小鱼,一条热爱文字的鱼。(经授权发布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