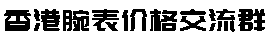一
清早出屋下楼,但觉天低云矮,水冷草枯,脸颊与双耳转瞬变僵,凛冽的风从领口与袖口等处渗入肌肤,整个身子都像堕下一方冰窟。我边走边想,人这生物的适应性也太可怜了:夏天怕热,冬天怕冷,温度稍高一点或低一点均受不了,也怪不得在博大宇宙空间总是知音难觅。
一步一步,我离开我的居所,走向离此约800米开外的我的供职楼厦。
我停在一株落尽了叶子的大树前,不经意地仰望东南边的天空,忽发现一朵彤云幻化成一个人型:发如一抹寒雪,眉眼棱角分明,竟然似曾相识,就那么默然地瞅着大树身前小小的我。我不由怵然惊悚:那不是我父亲的面容吗?
是的,那发型,那嘴唇,那眼神,那温情,那额角深深的抬头纹,还有那淡淡一弧老光眼镜镜框似的云影……
我有些泪眼婆娑了!
我忽然记起,今天是2018年1月13日。
1月13日,正是我父亲的忌日。他就是15年前的那一天永远地告别了我,也告别了他辛苦劳作过78年的这个世界!
云团缓缓散开,寒风依旧凛冽。
我想,难道冥冥中的父亲,15年来,仍会不时静悄悄地在高天上看着我么?
二
记忆的闸门缓缓打开。
我记得,父亲刚进入“古稀”之后,就明确意识到自己在人世上奔走与逗留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他思来想去,觉得这一世要做的最后一件大事,乃是为自己寻找一方墓地,构筑一份永远的“家业”:人生于世,一切赖以栖身的木楼瓦舍均不过是临时落脚的所在;只有墓地与棺椁,才称得上是恒久的归宿啊!
父亲请来阴阳先生,两人带一块镌有八卦图案的罗盘在山前山后转悠,终于经罗盘的指点敲定一方墓址。父亲置身其间,四面一望,发现自己北依大山之首,南对浩茫远天,东可观日出,西可避风寒,不由拍手称快。阴阳先生说:这大山蜿蜒回旋呈藏龙卧虎之势,,百年归山若能落脚于此,必主家族金玉满堂,必主子孙富贵有望,不过…… 父亲见先生欲言又止,急忙说:请明言。阴阳先生转动罗盘捻须沉吟三分钟,再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翻来复去念了好几遍,直起身一拍大腿说:唉,美中也有不足!你看这虽是龙首,却光秃秃地缺鬃短角,髭须缕缕脱落,加上坡坡坎坎不甚畅达,子孙的富贵怕也要经过许多坎坷磨难才会姗姗而至吧?假如这周围有一片林子,假如从老屋门口登山有一条七弯八拐的阴阳路,那该多好!听完先生的话,父亲暗暗确立了自己的行动计划,那就是:植一坡四季常青的松杉树,修一条沟通生死两界的阴阳路。
无需村官发话乡官批文,父亲说干就干。大年前后的消闲日子,他用树枝在雪地上划好标记,遂开始了艰苦的修路施工。雪粉在他的锄头上飞扬,冻土在他的脚踝边打滚,乱石草茎从他的身体两旁四散躲开。不久,一条坎坎坷坷的路即已蜿蜒在他的眼前。这条路的起点就在我家老屋的大门根,不出五十步即顺着山势弯弯拐拐地上,像攀附在崖壁上的藤蔓,一直抵达父亲为自己选定的那片墓地,真可谓名符其实的阴阳路。父亲高兴地说,他要走的最后一段路是他自己修的。其实,父亲走了七十多年的人生路,哪一段路又不是靠他自己走出来了呢?
路修成了,紧接着就是栽树。父亲托人从林业站购回大量松树苗、柏树苗与杉树苗,绣花一般在墓地周围栽成许多横的与竖的行子,然后顺着“阴阳路”两旁栽了十来棵道旁树。不几年,父亲墓址周围已长成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子,惟有正南方天袤地阔,遥对远山与云霓:父亲这人不耐寂寞,他要让自己终老后躺在大山里,仍能纵目骋望阳极世界那些层层叠叠的风景。
父亲的棺椁是用泡桐木合成的,他亲自用生漆涂得乌光铮亮。墓地选定了,棺椁备好了,父亲逢人就说:咱这一世,该吃的苦吃尽了,该受的累受够了,该享的福享到了,流过浪,讨过饭,挑过力,坐过牢,挖过蕨,种过地,上过私塾,做过手艺,闯过江湖,造过屋宇,能吸烟,能喝酒,能玩牌,能读书,能讲笑话,能哼戏文,能发牢骚,能在儿女面前摆弄老父亲的尊严…… 除了升官与发财,哪样的尘世风光未曾领略?七老八十,我死而无憾,唯一叫我放心不下的是,有朝一日无声无息地“去”了,儿女们东一个西一个满世界地漂泊,谁人将我置入棺椁送往墓地?我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地回到那个永远的“家”吗?
三
父亲回“家”的日子,是2003年1月13日,既农历壬午年腊月十一。当天凌晨,母亲一觉醒来,未能听到父亲旷日持久的那种哮喘声与咳嗽声,急忙打开电灯,发现他真正地无声无息地“去”了——父亲的瞳孔早已散开,父亲的肢体早已僵冷,只有嘴唇微微张着,仿佛是向黑洞洞的夜空呼唤着什么。母亲鼻子一酸,不由老泪纵流。她明白,众多子女没有一个为父亲送终,父亲临终竟然没能留下一句遗言,这人也走得太匆忙了,太孤独了,太默然无语了……
我在远离故乡二百多里的城市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父亲早已被邻居们穿戴一新置入了窄窄的棺椁。父母的子女中,我是长子,也是离故乡距离较近的一个,丧事理当由我来承办。当日午后,我坐在风驰电掣开往故乡的小轿车上,想到因公务繁忙生计缠身,最末见到父亲一面的时间也过去了几近一年。其间,没有任何通讯联络,仅仅在一个多月前,偶闻父亲从骡背上跌下来伤了筋骨,仅电话委托他人赶到家中问候了一声。父亲传话说,伤得不算重,经医生诊治伤势已愈,大可不必回家探望,不必挂肠牵心,你尽管忙你的公务好啦。如今想来,虽然是谨遵父命,但也负疚深深——父母的生老病死在我心灵的天平上是不是显得太轻了一些?父亲啊父亲,若真有所谓在天之灵,您能耐心地听完我倾诉那贮满心胸的忏悔之情吗?忠孝难两全,忠孝难两全呀!但我挤上一天两天时间回乡看看父母并不是全无可能,我实在是无法饶恕我的冷血心肠!
四
父亲回“家”的那天,离他78岁的生日尚有25天。78年,我的农民父亲用他的生命写成了一部普通山区农民生存与奋斗的史册。这史册,是父亲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产,它成就了我的文学才华,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
父亲出生于1925年1月30日(农历乙丑年正月初七),他是祖父祖母最小的孩子。父亲刚满3岁就失去了母爱,据说,祖母是大口大口吐着鲜血离开人世的。祖母去世后,父亲也曾在祖父支持下上过三年私塾,他对百家姓、千字文、增文贤文一类教材的诵记能力好得惊人,以至到了中老年仍能整段整段地背出和写出。不幸的是,父亲12岁那年,祖父因欠下累累债务被逼得典卖田庄,老人家忍无可忍,痛不欲生,于是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投缳树杈。成为孤儿的父亲再也不可能上学读书,遂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流浪生涯。他穿着编耳草鞋,挑着两只笆篓,走津市,赴常德,上云阳,下宜昌,足迹踏遍了湘鄂川边地的山山水水。少年时代,父亲曾在兵荒马乱的宜昌过了三个除夕,帮过工,讨过饭,挑过力,摆过地摊;父亲曾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的情况下修公路,修机场,亲眼看到他的伙伴们或在炸弹的轰响中血肉横飞,或在冻饿熬煎中毙命;父亲曾在挑夫的行列里突然遭遇“棒老二”袭击,导致他的一条右臂留下残疾,肘关节年复一年总是蜷曲着,一辈子也未能伸直……
父亲少小时离开失去了家的家乡,孤苦伶仃,漂泊无依,这种漂泊生活造就了他落拓不羁的性格。直到二十多岁后,父亲才辗转回到乡土,决定在安埋祖父祖母的坟地旁老老实实地结婚生子春种秋收过日子。据我的姑母回忆,父亲流浪回乡时已是面黄肌瘦,步履蹒跚,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连亲姐弟见面也互不认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乱世风云,兵荒马乱,世情沧桑,普通人生活与生存的权利根本没有最起码的保障,父亲对此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
五
父亲与母亲走到一起是在他二十三岁那年。
父亲是孤儿,母亲和她的母亲即我的外婆则是一所地主庄园里的无家可归的佣人。父母婚后,一间低矮的烟尘蓬蓬的老木屋成了他们相依为命的居所。就是在这所老屋里,先后诞生了我的姐姐、我和一个妹妹。我对那幢老木屋的印象非常肤浅,因为在我五岁时,老木屋就倒塌了,一堆破碎的糟木板与杉木片,竟是我对出生之所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印象。
父亲曾对我说,他一生犯了几个最致命的错误。其中第一个错误就是新中国建国初期,他主动放弃了参加工作的机会。土地改革时,父亲的成份被定为下中农,是工作队依靠的对象,更加之他上过几年私塾,初通文墨,可算是当时难得的人才。父亲被推举为区农会筹备委员,,宣传党的政策,参加各种会议。后来又被安排到离家五十余里的某药材场担任领导职务。那时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薪水,加上我姐姐已3岁,我刚刚出世,父亲割舍不了对孩子的思念之情,他工作不满两年,竟主动申请辞职要求回乡务农。父亲谢绝组织的挽留,企望趁当时田土到户之机努力发展药材以养家口。父亲说,他经营田土不几年,农村形势就由合作化而发展为人民公社化了。他原来的同事与部属一个个都成了“国家人”,而父亲则由于主动离队失去了工作的权利。父亲右手伤残,许多重体力劳动无法胜任,只好申请到街道上摆摊做点小手艺,给生产队上缴数目不小的副业款。
父亲所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在大集体时长期“不务正业”,。父亲凭着那点可怜兮兮的文化和他的小聪明,手艺的门类与时俱进,不断革新。最初,他为人理发和修补各类胶鞋球鞋,后来是修理手电、钢笔、汽灯和从事各种小五金的焊接工艺。再后来发展为修理钟表和雕刻图章。父亲的手艺和服务质量颇有名气,他走到哪里,那些同行们马上会门庭冷落,因此他总是遭人怨谤。特别是雕刻图章,其他同行习惯用一个大木卡子牢牢卡住章坯,先用毛笔反写成字样后然后落刀雕刻,但父亲从来不用卡子,也不用在章坯上写字,而是左手握住章坯,边与人聊天边执刀刻字,不到二十分钟,一枚精致的图章就雕刻出来了。特别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父亲写出的字离书法艺术相差老远,一点儿也谈不上耐看,而他用刀刻成的字样却美不胜收。只要顾客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无论正草隶篆,他均可小小印章上一挥而就。父亲一辈子用刀刻字的数量比他用笔写的字多得多。他雕刻的图章遍及恩施乡土,不少人以珍藏有他刻成的的图章为荣。
六
父亲说过,他这人生不逢时。从小是孤儿,旧社会是流浪儿;安家不久适遇社会变革,恰可大展宏图干点事业,又偏偏开了小差;大集体时常常是用数十几倍的钱来购买一份口粮,还不时成为批判所谓“资本主义”的靶子;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儿女渐成也渐散,又偏偏人老力衰,眼睛不再那么“灵光”了,其手艺不再吃香了,因为人们修理废旧钟表不如新购一只价格低廉的电子表,随着识文断字者增多,人们交易往来也不必盖章而改为多用签字。
父亲一辈子的爱好比较宽泛,喜欢读故事性很强的书,喜欢哼戏文,喜欢研究碑刻铭文。凡有新鲜东西,他总喜欢弄来研究一番。据说他学习修理钟表,就是省钱买来一大堆旧钟表拆了装、装了拆,反复揣摩。学习雕刻,则是用小钢片磨制刻刀后,斫来大量黄杨木磨成章坯试刻,直至刻完几麻袋章坯后学成的。我记得他曾用毛笔抄录成一大本汉字的正草隶篆字帖,供自己营业时备查,字帖上的字笔笔工整如刻印。他常备一个大本子,其上盖满他为别人雕刻的五花八门的图章式样,可惜我那时不懂得珍惜与收存!
父亲对我的要求极严,少小时,除学校作业外,每天还必须写毛笔大字若干、铅笔或钢笔小字若干,而且年年增指标,对我最终的要求则是至少初中毕业。有人笑问,那他初中毕业以后呢?父亲拍了拍他的手艺箱说,老子把这箱子交给他,一辈子吃穿不愁。
刚上到初中二年级,,14岁的我就成了回乡知青。父亲只好让我提前扛起箱子跟着他跋山涉水穿城走镇“讨生活”。两个月后,生产队强性将我收回,大概意思是老的有残疾,不能从事重体力,才允许他搞副业;下一代不能再跟着搞“资本主义”,。我无奈,只好随着男女劳动力早出工,晚收工。我当时喜欢写写画画,终导致父亲在清队运动中落下两条罪名,一是拖欠副业款,二是教子不严。于是,父子俩一起被“炮轰火烧”。愤怒的父亲曾亲手烧毁我除了红宝书之外的全部书籍文具,说让我从此老老实实地挖泥拌土就够了。多年后,父亲向我解释,谁有知识谁挨整,我烧书,实际上是在挽救你。我说,我懂。
我未能承接父业,父亲也许心怀怨恨,但我后来堂堂皇皇成了一个“国家人”,他还是挺高兴的。他曾说,老子一个小差,耽误了整整一代人,也好,总算在你身上补回来了!
七
其实,我成为“国家人”的道路艰苦异常。14岁失学后,,上了2年“半耕半读”式的区办土高中后再次务农,21岁时,我方成为月薪15元的民办教师。两年后,才过关斩将踏入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成为所谓“工农兵学员”。待到真正吃上“公家饭”,我已经是25岁的高龄青年了。
我步入教书生涯,对渐渐年迈的父母亲来说,除了精神慰藉,物质上仍谈不上多大帮扶。因为那时教师待遇极低,加上教务繁重、学历函授、弟妹求学、修房整屋、结婚生子、抚养义务等一系列人生功课接踵而至,除了经济状况总是入不敷出外,时间与精力对我也吝啬得几乎一毛不拔。废寝忘食、熬更守夜,深恐教务兼家务顾此失彼,对于我几乎是家常便饭。人生最灿烂的“而立”之年前后,我不仅而立未立,并且欠债累累,如牛负重。
1987年,我在一所乡村中学守岗10余年后由乡入城,从此,每年与父母相逢时间仅为几个小时而已。只发觉老父亲已渐渐远离了他所操持的手艺,苦苦守护着他年轻时辛苦经营的三间瓦房与后来落实到户的几亩薄地、一片荒山。父亲去世的前几个月,我刚好由某县城调往州城上岗,离家的路程更远,且出于想用拼命工作的劲头给新岗位领导与同事留下好印象,决定到年假时再回乡省亲。而恰恰离大年除夕只有十几天的时间里,父亲与我们、与人世不告而别!
八
父亲去世后的第8天,即2003年1月21日,在岳撼山崩的鞭炮声与鼓乐声中,我让亲邻将安放着他遗体的棺椁顺着他自己开挖的阴阳路扛抬上山,将他安葬在他多年前亲自选定的那方墓址上。父亲享年78岁,将近80载的悠悠世途,他东奔西走,阴差阳错,含辛茹苦,饱经风霜到白头,却把自己更为美好的期冀寄托在走完人生之路后的再生之旅。我不敢确定,人的呼吸停息后,是否真有灵魂这类物质仍会荡漾在茫茫时空?父亲是否真会在天上看着我一点一点地磨砺一介书生的生命晚景?
2004年的1月13日,风飒飒,雪飘飘,我曾肃立在父亲坟前,用一首《父亲周年忌日感怀》的诗作向他祷告并请他原谅,希望父亲懿德永芳,山高高,水长长。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父亲离世已经15周年,我也成了一位65岁的老人家!今天,我在异地供职,只好瞩目风起云涌的广袤长空,再度抒发自己刻骨铭心的追思怀想之情,愿父亲的灵魂安息在天上,欣慰地注视他的子子孙孙在广阔大地上,继续上演没完没了的人间喜剧。
父亲能够在天上看到我,我想他也必定能看到离乡土空间更加遥远的他的孙辈与重孙辈,看到此后生生不息的子子孙孙们再接再历,看到人类世界的沧海桑田、日月星辰!
父亲,愿您灵魂永驻!
2018年1月16至17日写于恩施凉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