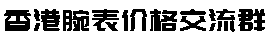
2021-02-15 14:52:15
2013年金秋十月,喜逢我的研究生导师、中国著名环境卫生学家、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孙棉龄先生九十华诞。在张天宝老师的感召下,我和师兄弟姐妹等一众弟子于当年10 月1日一起回到成都为孙老师祝寿。不少人彼此多年未见,相见甚是激动。每每回想起在孙老师指导下读研的三年以及毕业后和孙老师的交往,往事依依,历历在目,不禁潸然。
临去成都前,按张老师吩咐,仓促拾其一二,写了篇“难忘三载天府华西求学路,铺就师生一世绵长友谊情”的回忆文章,以祝愿孙老师健康长寿。拙作有幸被收录在非正式印制的几十本纪念册里。在公卫微信群发出部分内容之后,在华西公卫80级卫生专业学弟张祥的良言相劝之下,以这篇回忆文章为基础,经多次修改后寄给华西校友会编辑部,以期和更多华西校友分享,未尽如人意之处,敬请斧正。 是以为记。
投考川医
我是1979年从吉林省榆树县农村考入长春白医大卫生系读书的。出于对科学殿堂的向往,从大二开始便立志考研。77级学长、现在任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精神病学系系主任李新民教授告知我,要读研究生,必须从学好英语开始。这样,苦学英语便成了我的不懈追求。为强化英语学习,除课本外,还自学了上海第二医学院谢大任教授编的《医学英语》六册。
在学《医学微生物》这门课时,如念天书般地啃了一百多页的大部头免疫学英文原著。这样,大学入学从 ABC学起的我,大三英语结业考试时,在全年级300多学英语的同学里,取得了和另外四位同学并列98分的最高分的好成绩,为此后的考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同当今的精准医学一样,那个年代的“环境医学”也是个十分神圣的字眼儿。出于对这神圣的殿堂的向往,我决意考取环境医学方面的研究生。如此,老早就开始着手复习生物化学这门基础课,并收集抄写一切有关卫生毒理学方面的为数不多的参考书。诸如《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毒理学分册》,河北医学院吴沈春、于志恒两教授主编的《环境与健康》,还有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材后面的毒理学实验部分等专著。
虽然抄了“所有”资料,仍觉得不踏实, 又给中国环境卫生学的扛鼎人物、武汉医学院环境卫生教研室的蔡宏道教授写信,索购他们环境医学系内部用的环境毒理学教材。蔡教授回信,说他已委托他的研究生王新到教材科帮我购买邮寄教材。看到王新先生寄来的橘黄色封皮的崭新环境毒理学教材,想到这是一位知名的环境医学专家亲自回信并托付弟子亲自办理邮寄的教材,我倍加感动。为此,我特别写信给武汉医学院的校刊编辑部,表达了我对蔡老前辈的感激之情。把这本教材里环境毒理学的新内容揉进我摘抄的笔记里之后,立马感觉踏实了许多。
为了1984年考研,我早早就和和咱们川医的我国第一代环境卫生学家过基同教授、第二代环境卫生学家孙棉龄教授等全国部分高校卫生系和科研院所环境卫生和劳动卫生领域的大教授们写信表达报考意愿。咱们四川医学院的孙老师代表他本人和过老师亲自给我回了信,回信长达两页,对我的问题一一作答并充满鼓励,令人印象深刻。
由于过老师、孙老师在环境与健康的研究方向属于环境医学核心范畴,非常吸引我,而且考试科目与我准备的完全相符,这样,虽然对四川医学院的大名有些犯怵,但还是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咱们四川医学院。报考之后,又给先一年从白求恩医大卫生系考回川医的高宁师兄写信求教。高师兄就难度较大的川医生化以及卫生毒理,环境卫生两科的出题风格和重点给我回信点拨,对我备考帮助巨大。
经过孙老师和高师兄的指点和个人的认真准备,我在笔试各科都取得了较好成绩。考试完,高师兄帮我查分后回信说:“你的总分虽然第二 但你各科成绩均衡,无论怎么划分数线,你都应该没问题。”这封回信让我早早地吃了个大大的定心丸。要知道,这总分数第一名可是咱们川医卫79级美女、毕业后留校的张遵真同门学友呀。考上川医的难度可想而知。
(上图,高宁同学回信信封)
(高宁同学回信第一页)
(高宁同学的回信第二页)
复 试
命运的改变有时候就是这样的神奇。那封装着川医复试通知的小小牛皮纸信封寄到了我们白医大宿舍楼,但却不幸散落到收发室门前的水泥地上,亏得恰巧被我们班的两位善良胖女生吴同学、王同学路过时发现,随手捡起并及时交到我手里。如果不是她俩的善举,也许今生我也就无缘华西了,想想都觉得后脊梁冒冷汗。在此也特别感谢她们俩。
记得启程参加复试的那天是84年5月1日。我挎着智室友的退了色的帆布大黄书包,带着家在四川的美女刘同生的学生证,还有我表哥和同学借给我的 160块钱及吴同学、王同学给我买的崭新的黑色电子表,坐上先南下北京再转西行至成都的火车,开始了第一次出省的神奇兴奋希望之旅。
火车在东北平原和华北大平原上穿行。五一的长春,积雪还覆盖着大地。到了辽宁,雪就都融入大地了。进入河北地界,庄稼苗已长出。等到了河南的时候,满眼已是绿油油的、长得老高的麦苗。在陕西的黄土高坡上看到了新奇的窑洞。过了秦岭入川,火车在隧道和山麓间穿行,出了隧道就能看见绿色的山峦,涓涓细流从山涧缓缓流下,汇入从山脚下的峡谷里流过的嘉陵江中。江水映着山的碧绿、平缓地流动着,给人无限遐想。
进入川西平原,抵达成都的时候,恰逢雨天,蒙蒙细雨里,遍地都是黄黄的花 ,后来方知是油菜,农家小院各个翠竹环抱。经过近三天三夜从北到南的旅行,一路领略了四季景色,新奇极了。大约中午走出成都火车站,在站前买了一碗米饭和一盘麻婆豆腐。第一次吃川菜,辣得我不行,吃了一半就实在受不了了。
川医如画的校园,古香古色的典雅建筑加上和煦的阳光,瞬间就让人感觉时钟在这里都是慢悠悠的。和我们白医大的马路大学风格与雄伟建筑成鲜明对比。来到研究生办,一位个子不高、身材偏瘦的中年女老师和风细雨地接待了我。 办完手续之后她把我领到药学系研究生李森和王昌进的宿舍,把我安顿在那里。李、王两位同学是81级的研究生。李森个头不高,行走如风,透着自信与干练劲儿。他主动和我聊了一些闲话以使大家尽快熟悉起来。王昌进身材又高又壮, 走路说话都很沉稳。住在一起之后,目睹两位即将毕业的研究生早出晚归做课题的身影,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研究生充实繁忙的生活。
(以钟楼为标志的华西校园核心区域,注意,还有一弯明月高高挂在天上呢)
入学后不久在老图书馆旁的小校门边的布告栏上,就看到这两位学长的论文答辩海报。虽然专业内容和我的不搭界,因为有在一个宿舍同住几日的奇缘,出于好奇和尊敬就去旁听了。两位学长均用英文报告论文和答辩。李森答辩时赶巧没电,但他早就有应急预案 ,用事先准备好的、,讲一张翻一张,轻松自信、应对自如,足见李学长在四川医学院训练出来的功底。后来, 李森学长获得了圣地亚哥之加州大学化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法律双博士学位,如今是北京万慧达集团高级合伙人,已成知识产权界的翘楚,这是后话。
第二天复试,来到卫生系教7楼三楼环卫教研室宽敞而略显空荡的大办公室,我的导师过基同教授和孙棉龄教授已经在此等候我的到来。记得当时孙老师从一本环保方面的英文专业书里选了一页有关污水处理方面的文章让我翻译成中文。我接过书自信地问孙老师有没有环保方面的英汉词典,孙老师向过老师会心地笑了笑,感觉孙老师好像是在跟过老师说我还知道要个环保词典,就去隔壁的屋拿了一本给我。
复试笔试结束,过老师提出让我讲句英文。学了多年哑巴英语的我毫无准备,脱口而出说我不会讲。两位老师反复和风细雨地提示说讲句最简单的就行,比如你好,我要回去了,我说那我也不会。就这样,大家“僵持”着。已经记不清我是到了最后讲没讲呢,还是心虚小声地说了几个字应付了事了。留下的只有对我那一刻的窘态与偏执特别深刻的记忆。每每想起都很后悔,觉得当时自己不管怎么心虚和对与错都应该说上一句。这事儿给我的记忆值得回忆一辈子。
(华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本营---第七教学楼,亦名“志德堂”)
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到,过老师早年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得环境工程学硕士学位,英文特别好。就连后来的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卓有成就的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专家王瑞淑教授出国进修考察前都要主动和过老师在上下班的路上学习英语口语,可见过老前辈的英文功底之深厚。
选课题
在白求恩医大读书的五年,由于我只顾着准备考研、学英语,没有好好学习临床医学和实践。每次放假回到家乡望山屯,什么病都不会看,总觉得有点儿愧对江东父老。心想,现在我要开始搞研究了,可要好好选个课题做出点名堂。当过基同教授和孙老师问同门张遵真同学和我,是选环境毒理学方向还是环境流行病学方向的时候,遵真同学和我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环境毒理学研究方向。虽然隐约觉得两位老师特别是过老师很想让我做环境流行病学方面的研究,但是慈祥的过教授老前辈还是支持了我们的选择。就这样,我天天查阅着各种中英文环境毒理学方面的资料,一会儿贪大求全,一会儿异想天开,整天处于否定自我的状态无从下手。
期间还有个有趣的小插曲。一天,在学校图书馆里坐着那儿看文献,遵真同学也在图书馆看书。她看到我之后,就径直来到我面前站那儿和我说话。我俩说着说着,我上大学以来和女生说话就脸红出汗的老毛病又犯了,感到脸热心跳,大汗珠子直从额头往外冒,浑身不自在,心里只盼着她赶紧离开。可她站在那跟没事儿似的,就是不走,和我继续聊,我只好有一搭没一搭的和她聊着。聊着聊着,神奇的事儿发生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突然静下来了,整个人不再紧张不再出汗。经过这次休克脱敏强制治疗,我的这个毛病好多了。
(87年和孙棉龄教授、张遵真同学在华西钟楼前中轴线上)
读研第二年,进入了紧张的课题设计和试验阶段。同学们都在各自的领域有着飞快的进展。
张同学已选定用较难的体外细胞培养技术来研究新农药叶枯灵对细胞体外恶性转化的研究,并且大刀阔斧、披荆斩棘、雷厉风行地把细胞培养室从无到有地在教七楼一层的一个房间建立起来,经常骑着自行车奔波校外去取小仓鼠来用于分离和培养细胞了。
环境病理学的郑志仁教授是病理学的大家,在“矽肺”的病理解剖研究方面非常有建树,是全国知名的专家。名师出高徒,他老人家的学生谭建三室友也悠哉悠哉地都快把课题做完了。
我们卫研 84级年纪最小的、最漂亮“班花”徐培渝同学是劳动卫生教研室王宗全教授的学生,整天出入教7楼Ground floor肖邦良老师的免疫组化实验室,一边和李琼英技师形影不离有说有笑,一边进展神速地做着她的实验。
卫生统计学的老前辈祝绍祺教授和《卫生统计学》主编杨树勤教授的学生潘传旭同学除了完成学位课题外,已经随着课题进展,,赴美调研考察,出色完成随团翻译任务后载誉而归了。
(87年卫生系84级研究生在九教学楼前合影)
(和卫生系79级、研84级同学牟华在一起)
相比之下,我这儿还一点着落都没有,不禁心里很是着急起来。孙老师也很着急,他看出了我“眼高手低”的毛病, 提出让我做个农药一般毒性方面的课题,因为教研室在这方面基础较好,所以课题比较起来相对较容易,但是我没有接受,孙老师也没有强求。这时我也意识到自己的毛病了,决定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在课题设计上下功夫,争取用达到一定理论高度的办法解决问题。
联想到农药叶枯灵是防治水稻白叶枯病的,我国水稻主产区在南方,这些地区食物受黄曲霉毒素污染严重导致肝癌发病率较高,推测叶枯灵和黄曲霉毒素在人体内有相互作用的可能性。于是我决定用我们教研室衡正昌讲师建立起来的非常成熟的艾姆斯沙门氏菌致突变试验技术来研究农药叶枯灵对黄曲霉毒素致突变性的影响。利用叶枯灵,黄曲霉毒素与肝脏富含代谢酶的微粒体的加减和先后作用顺序的变更,将农药代谢以及黄曲霉毒素的直接和间接致突变性柔和进去,以期达到全方位模拟肝癌高发现场的真实环境。
这样考虑一番之后,我觉得这个课题可以避开我动手能力差的弱点,理论上复杂多变,有很多可写的内容,对现实工作也有一定指导意义,所以对自己用这方面的研究做研究生课题设计信心倍增。这时,适逢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的刘毓谷教授来华西,要和孙老师见面,孙老师就让我当天晚上到他家跟刘教授讲讲我的想法。刘教授是我国环境毒理特别是毒物代谢方面的权威,去见刘教授,心中充满着紧张和不安。胖胖的刘教授非常和蔼,可是仍不能缓解我紧张的情绪,我也就三言两语把我的想法跟刘教授讲了。刘教授跟孙老师说他觉得可以,我则如重释放,飞快地离开了孙老师家。
(88年和刘毓谷老师在石家庄)
做课题
题目定下来就得赶紧做了,大量的实验工作是从七教学楼背后那个灰砖三层毒理楼二层的大实验室开始的。这时,教研室分给我两个刚来的年轻进修生,,一位是重庆三军医大环卫教研室的叶建锋让我来带。,长的一张干净的娃娃脸,但说话声音已展示了青春期大男孩变粗的声音,为人低调谦和。 叶建锋也刚大学毕业,是个健谈活泼的小帅哥,所以深得教研室老师喜欢。连孙老师这样的资深教授,都愿意和小叶聊天,聊小叶他们科主任卓建波教授。孙老师和还是卓教授是大学同学呢。
带他们的第一项工作是把洗好的玻璃瓶瓶罐罐和吸管包扎包装好放入高压锅消毒。开始小杨和小叶二位还李老师这、李老师那地请教个不停,以图我给予他们指点。当他们看到我那手足无措,不敢与他们四目以对,不知从哪下手操作的窘迫样子,小杨就接过我手中的活,反倒和风细雨地手把手教起我来如何将棉花塞堵吸管顶部然后再如何把多个吸管用报纸包扎起来放到高压锅里。
回想起来,,虽然不知道你今天在哪里工作生活,但我要真诚地说一声“谢谢你!”是你第一次教会我如何在实验室独立工作,令我终生难忘。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们二位进修结束时,还联合买了本影集,写上赠言签上各自的名字作为礼物送给我这个“老师”。
随着课题进展和忙碌的实验,自己心里踏实起来,也倍感充实和愉悦。但天有不测风云,这美好的工作学习过程很快就被令人懊丧的失误打断了。
记得是个周六,为准备下周一的大规模实验,我在实验室忙了一上午。最后一件事是将高压消毒好的十来件白大衣放入烤箱烘干两个小时。刚好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我给烤箱通上电便回宿舍吃午饭。吃完饭,也就把烘箱里正烘着白大衣的事儿忘到了九霄云外。下午和谭建三和牟骅两位室友,还有很多人在人民南路三段的校门附近集合等候准备去哪儿看电影。等着等着,我突然心里一激灵,想起我的白大衣还在烤箱里烘烤着呢呀!来不及和周围任何人打招呼,一路奔跑冲向校西区的毒理楼,跑到楼背后的马路上时看到实验室的窗户都是雾蒙蒙的。当我冲进实验室,室内已是烟雾腾腾,糊味扑鼻。我赶紧拉断墙上电火花直迸的电闸、打开烤箱,接水泼向浓烟直往外冒的白大衣。火被扑灭了,从烤箱里拿出来的黑乎乎、湿漉漉破烂不堪的白大衣足足装满了一大盆,看着真是揪心和后怕。想到下周的重大实验和好不容易约好帮我的多位老师和技术人员,我当即决定赶紧利用周末买布赶制白大衣。
作出决定之后,我赶紧跑到衡老师家借了钱,又跑到西校门附属医院附近街边的寿衣店铺买到白布,并让店铺赶制白大衣。到了周日傍晚,我已将十来件全新的白大衣取回挂到无菌间,整整齐齐一大排,甚为“壮观”,个中滋味五味杂陈,只有自己才能体会。星期一上班,大家看到墙上挂着的一排新白大衣,再看看地上一大盆形同抹布、糊味未消的白大衣,一下子就全都猜到发生什么了。
当晚,教研室副主任杨在昌老师特意来到实验室单独向我了解情况,推心置腹地讲了好多话,但没有批评我。我怕孙老师担心,没敢把烧毁白大衣的事告诉他,可孙老师还是知道了, 弄得他很被动。 孙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趁着没人把我好一顿批评,问我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恩师就是恩师,生气归生气,气过之后,他老人家又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用命令的口气让我拿着还给衡老师。
论文答辩
经过长时间翻来覆去、集思广益的讨论、思考,在扬长避短地选定课题之后,经衡老师的技术指导,在朱振华老师、李质胜老师各方面给予的关爱之下、还有吴老师无偿提供的充足进口关键试剂黄曲霉毒素 B1,加上张天宝老师的参谋和讨论,毕业课题基本上满足设想,有惊无险地按期完成了。在经历了无数个挑灯之夜, 独自一人信心十足地奋战在毒理楼那间可以称之为家的大实验室奋笔疾书之后,毕业论文也顺利撰写完成。
其间张天宝老师经常在傍晚时分来实验室和我交流讨论,出了不少点子,激发了很多思想上的火花。由于资料准备和占有充足、实验设计充满变幻且无遗漏,很快拿出自己比较满意的初稿。
(87年毕业前夕,在华西医科大学大校门口留念。大门门头上高挂总设计师亲笔题写的“华西医科大学”五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时光荏苒、待到我们研究生毕业时,四川医学院已经恢复了“华西”的名号,。每次从大校门走过,看着题写的校名,自豪之情油然而生。当年学校规定,学位论文必须用带有“华西医科大学”抬头的方格稿纸书写备案。我自己书写了一份,曾祥贵老师说我抄写的就可以,可我还是请谭室友推荐的一位女士来抄写最终版本。最后采纳遵真同学建议,请孙老师书写封面。孙老师用一支纤细的毛笔,一笔一划地填写了论文题目和研究生姓名等信息。
筹备论文答辩首先要安排处理一大堆琐事,确定需要秘书一职。孙老师特请曾老师来担当秘书。那时候,曾老师刚刚以秘书身份忙完学友的答辩,所以他很犹豫。孙老师就对曾老师说,你是大师兄,就麻烦你再辛苦一次吧。曾老师实在推托不过,便接过了这个苦差。
论文答辩委员会由华西肿瘤所的罗德元教授、我们实验室楼上的卫生毒理教研室主任李寿祺教授、营养与食品卫生的徐维光老师、川大生物系的王老师、我的恩师过基同教授和孙棉龄教授等“大咖”组成,阵容蔚为壮观。圆圆胖胖、和蔼可亲的的罗教授担任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川大的王老师作书面评议。
答辩前,朱振华老师悄悄跟我说,楼上的李教授看了我的论文后在他们科室表扬了我的论文,让我不用紧张害怕,听到这个消息,我情绪一下子稳定了下来。答辩那天,劳动卫生学专家,时任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的王治明教授代表公卫学院首先致词,然后答辩会主任罗教授请导师介绍研究生。在王院长宣读致词时,孙老师前倾的身体和聚精会神的聆听的样子以及他本人介绍我时的严肃表情,我的室友谭建三兄长紧锁眉头、正襟危坐听讲的样子,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论文答辩时的照片,记录下了关心我了解我的老师同学替我捏把汗的那一珍贵瞬间,用时髦的话来说真是“有图有真相”呀。还记得毒理的胡渝华老师在我报告完论文之后问了一个不太难的问题,我轻松作答。最后经答辩会成员闭门讨论后罗教授宣布论文被各位答辩委员给予全 A通过,让我喜不自禁。几年的辛苦,总算是有了收获。
(时任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的王志明教授的代表公共卫生学院致辞,左起孙棉龄教授、罗德元教授、李寿祺教授、徐维光副教授)
(答辩委员会成员。左起,过基同教授、孙棉龄教授、罗德元教授)
毕业道别
在华西坝,充满苦辣酸甜的三年求学生涯,一晃就结束了。在这里,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古老”的华西的人杰灵秀和文化底蕴。在钟楼下、在荷花池边、在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一至八教学楼里、在学校礼堂,有着老教授合唱团精彩的演出和数不清的英语讲座。许多老师都是个性鲜明、神采飞扬、让人难以忘怀。诸如讲话飞快我很难听懂的免疫学王惠文(?)老师,英语课上周维新老师的精神饱满眉飞色舞大汗淋漓,口腔学院王翰章老教授的山水画,生化蓝天鹤老教授的浪漫爱情故事,我国乡村卫生学始祖陈志潜老教授的美丽传说,外教老师布朗太太的和风细语,还有锦江河畔的英语角.....在这里我收获了人生旅途上的最珍贵情谊。
永志难忘曾经和过老师一同在校园漫步,孙老师手把手教我们学英文打字,谭建三兄长室友把我纳入他的腋下无数次到他家度周末吃火锅郊游,和同门张遵真一起切磋英语......这诸多无比甜美的瞬间,都留在了我脑海深处......
道别是在环卫那间大办公室举行的,沿墙四周坐满了环卫的全体师生。道别会是怎么开始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临别时走到每一位老师和同学面前道别,走着走着,我就泪眼婆娑了。待走到孙老师面前时,早已是声带哭腔,不敢直接面对,和孙老师只有一霎那的对视,就匆匆离开那个大房间。
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在经历着和老师同学分别的痛苦时刻,惊喜又悄然来到身边。从成都去石家庄,来到我选择的工作地--河北医学院新卫生系报到那天,我独自一人下了火车,惊讶地看到度蜜月旅行的杨卫东师兄特意走下火车来到站台和我话别,令我喜出望外、十分感动。
毕业后的交往
再次见到恩师已经是几年以后了。最早的一次应该是在91年冬天,孙老师到北京出差, 我那时在中国医科院肿瘤所读博,特意带上后来成为我妻子现在是我老伴的女友到南纬路预防医科院招待所看望孙老师。孙老师离开北京那天,我又到老北京站送孙老师,一起照了相。
(91年冬季,在北京火车站送别恩师孙棉龄教授)
此后的2007 年,我又利用两次到成都出差的机会,面见了我的老师们。
第一次是春天,匆忙中只见到了吴德生、曾祥贵、张浩、和刘刚四位老师和已成教研室副主任年轻的王津涛老师。在新楼的实验室里守着一台显微镜随意地留下了一张难以复制的珍贵照片,因为没过多久,吴老师便因病告别人世。
这一别华西二十载,突然回到成都, 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好奇,立马走进位于人民南路上的大校门内的华西坝主校园。路边驻足看一眼“新”9 教和“新”图书馆,望一望钟楼。又到老校办公楼和老图书馆之间“栀子花径”上走一走,意外惊喜的是看到我们教研室原来的技师,当年对我厚爱有加十分关照的李质胜老师。李老师捂的严严实实,在老伴的搀扶下散步。得知他们的女儿,当年的瘦小小女孩,如今已在华西念大学了,我高兴不已。没过几年,科主任遵真同学发了封邮件说李老师已因病告别人世。
第二次是在夏天,专门到光明路家属院孙老师府上看望。师生多年没见,彼此都激动不已,相谈甚欢。孙老师特意找出三脚架,让师母胡老师给我们拍了几张我和孙老师交谈的合影。照片效果很好。后来听胡老师讲,八十多岁的孙老师亲自将胶卷送到照像馆洗出。
(2007年作者在恩师孙棉龄老师家中与孙老合影留念)
(2007年在孙棉龄老师家和同学张遵真、恩师孙棉龄老师合影)
再后来,这些照片很快和一封孙老师用娟秀的字迹亲笔书写、字里行间透着浓浓师生情谊的信函一起寄到我们公司在北京的办事处。
再再后来,得知孙老师的小孙女在我的“美国家乡”匹兹堡上学,我趁送我大儿子上学之机,给她带去点儿四川口水鸡以示关怀。 过后,她打电话说我带给她的口水鸡很好吃。人生奇缘就这样从两代师生开始变成三代人间的友谊了,真的好神奇!
(11年作者和家人)
(13年作者和张天宝老师在华西)
编辑: 云朵
相关推荐
友情链接
Copyright © 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香港腕表价格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