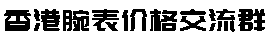城市啊有点脏
路人形色匆忙
孤独脆弱不安
都是平常
你低头不说一句
你朝着灰色走去
你住进混沌深海
你开始无望等待
楼与楼之间,一方未被光影占据的空间,七八个灰色的影子在白得刺眼的墙面上迅即掠过。抬头,想不到冬日的光,也这般灼烈刺眼,温暖和强度都让人不敢仰望。天空的鸟儿可以极目追逐去处,直到天边,墙上的掠影却转瞬即逝。
光,把影子不容反抗地投向寂寂的留白,任意裁切,自由变形。一缩再缩,一团再团,最后围着一个点打转,失去了延长、拉伸再延长的过往。
从中环到庙街虽说只有三站路,却消耗了傍晚所有的光,影也跟着消逝了。黄昏将至,夜幕降临,临街的店铺被店主装扮的光彩夺目,麻将馆和大排档招牌上的霓虹也都争相闪烁,灯光与灯光相连,将整条街道照得通明,伴随着专属港人的生活节奏,上演着商贩与顾客讨价还价的戏码。
街尾的兴记茶餐厅,包围在两边麻将馆的霓虹中,灯光显得暗了很多,但生意却依然火爆。环境依旧脏乱,仍然是多年前那副市井的模样,花地砖,老吊扇,就连“兴记茶餐厅”五个字都依然是当年最流行的美术字体。
不大的室内,人声鼎沸,聚在一起谈股票的;抱着孩子喂奶的;敲着桌子叫餐的;围在电视机前看的,喧哗中总能听到一声叹息。然而这样的环境里,也会有人在写稿或者读书,丝毫不受打扰。
香港就是这样,不像大陆,做什么都有圈子,在这里是没有圈子的,无论什么都是混迹在三教九流之中。
“阿洽,点解你?”,柜台里的阿仁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迈着蹒跚的步子从柜台里走出,赶忙过来招呼我。紧挨着门口找了张桌子坐下,寒暄了一番。
“回来搞咩?”
“搵你叹早茶啦。”
“你系咁幽默。”
阿仁的父亲是社团里的人,十五六岁就在庙街上“行古惑”,穿着背心或者过大的衬衣,腰后别着报纸,报纸里暗藏一把西瓜刀,没事就坐在茶餐厅“讲数劈友”。
那时庙街的天棚下,充斥着悍然卖翻版DVD的青年;操着内地口音公开卖假名表假名牌的女人;兜售和性用品的大叔……甚至一些隐秘的电子产品,阿仁就是在这个鱼龙混杂的环境里长大的,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行古惑”,在一次社团争斗中被打断了腿,后来就开了这间茶餐厅。
其实说到“港味”,我觉得就是这市井的烟火气,以及烟火缭绕里的活色生香,这里面一半是俗,一半是雅,说不上这是矛盾还是统一,可它就是无处不在,香港就是一个在烟火气和国际范之间不停切换的城市。
由于好久没见,,又谈到香港的市井。不觉间已经是凌晨四点了,刚好到了吃早茶的时间,店里陆陆续续上了一些客人,也都在这烟火气里开始新一天的生活。
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老头走了进来,浓密的胡须已经遮住了苍老的面庞,向跑堂要了一份虾饺,喃喃自语地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我问阿仁他不是街头的张鞋匠。从阿仁口中得知:张鞋匠的儿子考上了大学,结果得了白血病死了,张太也跟着过去了,从那之后张鞋匠精神就不正常了,每次过来都是只要一份儿子生前爱吃的虾饺,坐在那里自言自语。
大老远就能望见一个圆圆的招牌,用霓虹装饰的“鞋”字,蓝白相间的编织袋修剪的雨棚,雨棚下面还挂着一个木制的横牌“张记皮鞋”,旁边还有“男女童鞋,价廉耐用”的小字。
木讷的张鞋匠每天就是坐在店里,手里不停地做着鞋子,对每个人都会露出微笑,然后点点头继续手里的活,张太也会在店里帮忙打理其他的,偶尔也会和街坊四邻唠唠家常,或站在店口迎儿子。
生活虽然结局,却也是其乐融融,儿子很争气,每一科都是优优优,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也成了整条街的骄傲。每到吃完饭的时候,街坊邻居都围在一起,一看到他们家吃虾饺,就会有人讲“又得了优啊!”,张鞋匠就会很开心的一笑,点点头。
生活有时真的很捉弄人,没得选择,悲欢浮沉都要去接受。
“你个死鬼,躲远点,不然一脚把你踢到尖沙咀。”
“阿仁,叉烧包!”
“哇,阿洽,发达了啊!”
吼声打破了我原本的记忆,眼前穿着老旧的丝绒旗袍,染着枯黄头发,画着青黑眼线,涂着劣质红唇的女人,竟然是当年的梅姑。年轻时候的梅姑在庙街可是出了名的,几乎每个男人都想搂着她睡一觉,而现在却已没有了当年的风韵。
梅姑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习惯了花天酒地的生活,逃难来到香港之后,和当时驻港英军中的一个雇佣兵结了婚,过着平淡温饱的日子,每天至少有叉烧包吃。
香港回归之后,这些雇佣兵被英国人“遗弃”在这个城市,失去了原本英军身份所带来的优越感,生活一下子变得局促和彷徨,男人没多久就找不着了,原本就不算“家”的家,只剩下梅姑一个人。
没了生活的依靠,年龄不小的梅姑也只能穿梭在各个麻将馆中,做起了暗娼,在两旁的旧楼,黑暗的楼道深处,靠出卖肉体赚取生活。但依然是浓妆艳抹的,也是唯一一个穿着旗袍来店里吃早茶的,每次都会被人调侃,而梅姑却总是不屑的目光。
我原本是不相信梅姑是做暗娼的,直到那一次,梅姑拉着一个男人的腿,被拖着出来,衣衫不整,嘴角还有血丝,冲着那个男人喊“为什么不给钱”,男人回身给了她一个大嘴巴子,“都这么老了,给什么钱”,便扬长而去。讨钱未果的梅姑一边整理衣衫,一边冲着围观的人破口大骂,从那之后,梅姑就变了,每天都会和周边的人开着有荤的笑话,也调侃过我。
后来,她乡下的一个侄女瞒着家里的封建父母,为了求学来到香港,就寄宿在梅姑的家里,打过几次照面,看得出很单纯很上进,不过后来遇到了一个富家公子,在物质金钱的诱惑下,慢慢沉沦了,也变的热衷于享乐主义的声色犬马生活中。
被富家公子甩了之后,嫁给了一个年过半百的富豪,没两年老头就死了,而她却没有分到一分钱,再来梅姑这边却被梅姑大骂了一顿,从那之后再也没见到过。
她们或许只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也只是代表了那个时代女性普遍的一种现象,本来抱着一定的希望,能闯出自己的天地,但到最后却选择了妥协,香港当真如张爱玲笔下那样,一个令人心碎的地方,在华美的外表下,其实埋藏了许多悲凉的故事。
庙街只是香港的一个角落,有它神秘甚至黑暗的地方,却也有它不可代替的地方,市井里的烟火气也只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住在庙街的草根其实与住在中环的精英一样,都有着自己一套风格化的生活,俗趣也好,雅致也好,却侵染于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也许只有真正来过,才能体味出它的别致,它的美学味道。
暂别了阿仁,驱车赶回住处,日光正烈,横贯空中的电线杆也在地面上留下了工整的构图,成了富有诗意与乐感的线条。楼与楼之间也相互投影,用影子放肆地去抚摸对方的窗格,偶尔几只飞鸟从中穿过。
生活的一切,无非是光和影,有人在阳光下,低着头只看见阴影,有人在阴影里,往远看全是阳光。面对生活中一切的无奈和不快,只需向前走一步,让心灵充满光,把影踩在前行的步履之下,这才是应取的生活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