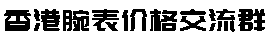文:藍天宇
7月的正午,酷暑炎炎。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康本國際學術園大樓前,準備過一個窄約10米的路口......
香港自開埠以來,來自中國內地的移民一波接一波地到來,人口數量呈現持續的增長。
尤其是1945年後內戰,使香港人口增長到1950年的200萬人,,這使得香港始終存在人口膨脹與土地資源稀缺的矛盾。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採用高密度發展的策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解決大量人口的住房與就業問題。
目前,香港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住在政府公寓中,戶型最大的69平米(以使用面積計算,下同),最小的只有8.2平方米。
以中國建築國際在啟德機場原址上建設的啟晴邨為例,最小戶型為14.1平方米,可供1~2人居住,每月租金不到1000港元,最大的37平方米,為兩臥室單位,可供4~5人居住,每月租金為港幣2387元。而像啟晴邨這樣的房子,正常需輪候3年以上,才能獲得資格。
除政府公屋以外,其餘均為私人開發商開發的屋苑,也大多數以小戶型為主。
據統計,全港只有10%的住宅單位大於100平方米,即所謂的“千尺豪宅”;而這些豪宅絕非普通人所能承受,如港島區100—160平方米之間的戶型,成交價近18萬港元每平米。
絕大多數港人的住房條件都不寬裕,一個小家庭常常住在50平米內的小房子,是很常見的事情。
有一段時間,,我頻繁往返於香港和北京,每一次到達首都機場,都感覺北京特別空曠。
不僅機場空曠,我借宿在朋友在三裡屯附近的社區裡,總覺得每棟房子頂上都可以再加十幾層,幢和幢之間也可以塞下更多。
朋友給我安排的10余平米小房間,感覺特別寬敞。
在北京,就回到那個宏大的城市尺度中,無論是戶內、社區還是市政道路。
在北京我會自動切換到大陸的生存之道——停止步行,上車,開始在各條環路上跑。可是,道路雖然寬闊,但道路卻是阻塞的。
而香港選擇的高密度的發展模式下,城市空間是令人壓抑的(尤其在仰望天空時),但你也會發現雖然道路不寬,交通卻遠遠好於北京,除了一般人很難承受的私家車,人們還可以選擇更多的出行方——步行、地鐵、巴士等等,快捷而又不失尊嚴。
對於如此窘迫的空間,沒有在香港生活的人根本就無法想像,大多會對香港人報以深切的同情和憐憫,甚至有一些內地的政府官員原本是來取經的,但看完之後往往會覺得不以為然甚至嗤之以鼻。
人們會好奇,在這種高密度的城市之中,這日子該怎麼過?他們會不會被憋屈死?
香港近年的自殺率約為十萬分之11.8,國際平均水準為十萬分之10~11,,中國內地為十萬分之23(非官方統計,官方資料欠逢)。從人均壽命來說,香港平均壽命82.8歲,為全球各地區第一(中國76.1歲)。
當然,這些事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至少說明空間未使香港這些指標相對其他地區顯著惡化。
一生好運,獨尊武神趙子龍
百戰不殆,當成功已成為一種習慣。
私人洽購請致電133-28-77772 聯繫大公館畫廊葉小姐,或點擊本連結訪問內頁索引
我們來開一個腦洞。
如果通過提高容積率、降低套均面積和壓縮道路用地等方式,將北京的人口密度提高到原來的四倍,那麼所佔用的土地面積就會縮小到四分之一,當一個圓圈的面積縮小到四分之一的時候,圓到圓心的距離也會縮小到原來的一半,也是就會帶來很多連鎖反應:
第一,原來必須開車或坐車到達的目的地(如商業、醫院、電影院等公共設施),就落入了人們的步行範圍,借助共用單車即可出行。
第二,地鐵或公交運營線路的長度縮短一半,減少了人們的乘車時間,同樣多的車輛和司機可以加密開行班次到原來的兩倍,從而減少了等候時間,每輛車的乘坐人數減少,從而提高乘坐的舒適度。
第三,當更多的人選擇步行或公交,放棄自駕,需要佔用的車型路面更多地讓給公交,也使公交更加準時便利。
第四,利用高密度的客流,讓地鐵和公交本身成為一項賺錢的生意,賺錢就會有競爭,從而改善服務,尤其是地鐵還可與零售業、服務業互動,獲取利益的同時也改善候車環境,同時政府不再為公交投入巨額補貼,間接為納稅人節省了開支。
第五,由於高密度的發展,車位元配比嚴重不足,停車費(我見過有80港幣一小時)、停車位費用(平均價格127.99萬港元)高昂,再加上高油價(約15港元每升),壓制私家車的增長。
所以,以上其實不算是腦洞,就是香港的現狀。
香港採用的高密度發展策略,在今天飽受各界詬病,其實也是整個歷史進程中的一次“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如果不採用這一策略,城市的邊界將被無限制擴展,而香港卻不是北京,地理上不允許無限擴展。
今天,高密度策略的實施成果之一,是城市留下500平方公里的“受保護地區”,其中包括24個郊野公園和22個特別地區。
這些郊野公園北京也都有,但不同的是,北京要開上1小時的車才能到的地方,在香港,人們可以從住處快速抵達,而且是真的郊野而非人造公園。
以灣仔為例,從任何一個地方出發,人們都可以步行幾分鐘至十幾分鐘即可上山,在長達50公里的港島遠足徑上行走,欣賞山峰、樹林、水塘、島嶼、蜿蜒迂回的海岸線和豐富的植被,在自然中行走,安全且沒有機動車的打擾。
而港島徑僅僅是四條遠足徑中最短的一條,最長的達100公里,此外還有無數的家樂徑、郊遊徑、自然教育徑等供人們選擇。
郊野公園的設置和建設,也已經被深圳市政府納入市政建設,每到節假日已經可以看到如織的背包客在深圳的山水間享受這一便利。
深圳同時吸納的另一政策是——圖書館之城。在北京一共有25個公共圖書館,相當於約90萬人公用一個,而小小的香港分佈著超過70間大型公共圖書館,相當於每10萬人就有一個。
圖書館全部分佈在居住點的周圍,步行即可到達,甚至一個小小的南丫島上都有兩間。在管理上也非常人性化,不設置任何門檻,讓所有人都可以補充知識,享受知識的樂趣。
和圖書館類似的是體育設施的建設,大多數也可走路到達,使用率極高。
回到開頭的故事。
7月的正午,酷暑炎炎。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康本國際大樓前,準備過一個窄約10米的馬路。
有四、五台車駛近,並緩緩減速。我停下腳步,揮揮手示意他們先行。最前的那位司機,隔著玻璃對我點頭微笑。中間的一位司機,搖下車窗,熱情地對我說:“唔該你啦(麻煩你)”。
當下,我的腦海中閃回了幾個瞬間——
在杭州街頭,停車等我過馬路的公車。
在新大阪站外,主動給我引路的遛狗大叔。
有一種說法叫“一切初遇都是久別重逢”。
我很迷信這個說法,並且聽到過一個很好的解釋:按照龐加萊回歸,有一定的概率,萬物周而復始。
講幾個朋友的小故事。
有位墨西哥朋友,35歲,亞洲行途徑香港。有一天我們在九龍公園裡面散步乘涼。她找到了一種“仿佛在洛杉磯的Angeles Knoll(500 days of summer取景地)”的重逢感。
另一對比利時CP。香港是他們環球旅行的最後一站。我們坐在中環碼頭吃著三明治,他們說:這種安逸和舒適,和他們倆剛剛在一起的時候,坐在安特衛普海旁的感覺一模一樣。
一座城市的溫暖和用心,就是在用極大的基數去中和這個概率,更多的給人提供“重逢感”。
一個正常社會的市民,無論殘疾或是健全,都必須擁有基本的生活權利、方便與安全,而政府的責任就是保證每一個市民生活都能維持一定的水準。
基於這一點,必須予以香港政府以肯定。
歷史的車廂,只給香港卸下了1000多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在這裡,人們享受不到寬裕的房子,卻為他們打開了一片更高更大的天空,讓人們走出家門,看得更遠。相反的,在北京在大陸的很多大城市,人們享受這寬敞的個人空間,就要忍受擁堵的交通、污染的空氣和低劣的公共服務。
城市選擇了自己的發展方式,人們就會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但是沒有一種選擇是十全十美、只有優點沒有缺點的。
只是對於特大型城市而言,高密度、緊湊型可能是城市化發展模式的一個必要選項。(藍天宇 / 王雅媛港股圈)
文章来源:王雅媛港股圈,點擊本頁左下角可以繼續“閱讀原文”。
版權聲明:「中環陸羽茶室」除發佈原創市場投研報告以外,亦致力於優秀財經未能及時與原作者取得聯繫。若涉及版權問題,敬請原作者添加DGGKF2微信聯繫刪除。
一生好運,獨尊武神趙子龍!
百戰不殆,對他而言成功只是一種習慣
私人洽購請致電133-28-77772 聯繫大公館畫廊葉小姐,或點擊本連結訪問內頁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