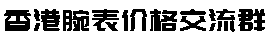《细读》杂志由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公众号以《细读》杂志为基本平台,致力于推介各类“细读”文章,开辟一片以文会友的校园地。
本期为书影心声专栏,推出吴青青副教授的《香港经验的影像建构——关于王家卫‘花样年华’》,本文发表于《细读》二零一五年春之卷,感谢吴老师授权。
作者简介:
吴青青,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博士毕业,现为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由文学转至电影学,目前主要学术兴趣领域在类型电影研究、港台电影研究等。
王家卫的电影是很特殊的。虽然王家卫不断变换影片类型,但他的任何一部电影都与一般意义的类型片截然不同。《旺角卡门》中表现的不仅仅是热血男儿的英雄豪情;《阿飞正传》也不同于寻常意义的飞仔片;《重庆森林》中有警有匪,却不能与警匪片相提并论;《东邪西毒》与普通的武侠类型电影相距甚远;《堕落天使》里的杀手与阴谋毫无瓜葛;《春光乍泄》讲述的也不是纯粹的同性恋;《花样年华》和《2046》似乎讲述的是爱情,却与有情人终成眷属毫无关联。王家卫的电影又是最具香港特色的。从《旺角卡门》一直到《2046》,他的电影从未脱离过香港的现实和香港的历史。“香港只是一处逃避动乱的地方,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自然谈不上归属感。生于斯长于斯的新一代,虽有较强的本土意识,却又与中国(历史)更为疏远……旧的历史被有意无意地压抑,新的历史意识又无法正常地滋长。”【1】久历的香港对自我身份的无法把持,不论历史、文化的无法定位的流离、无根感觉在他的电影中不断被重复。淡化故事的叙事特征和恍惚流动的镜头语言,在标识王家卫独特的电影艺术特征的同时,也表征着香港的独特历史体验和文化经验。
在某种程度上言,《花样年华》完全具备了一部情爱类型影片必须的叙事动机和情绪元素,但是,如果仅仅把它当作一般的爱情片,而忽略影片独特的情绪营造和影像建构,《花样年华》的故事情节不仅是单薄的,甚至是平庸的。王家卫在《花样年华》片尾“特别鸣谢刘以鬯先生”,影片中的几段字幕也是引自刘以鬯的小说《对倒》。《对倒》是一个从上海移民到香港的中年男子淳于白和一个在香港本土长大的花季少女亚杏一回忆一现实的意识流动,与其说电影改编自小说,不如说是小说的平行对应的叙事结构,给予王家卫的灵感启示。《花样年华》中苏丽珍和周慕云在狭窄楼道间的多次擦肩而过,镜头语言的重叠对称,显然来自“对倒”【2】的意境。
然而电影中复杂暧昧的香港经验,和王家卫的其他电影是一脉相承的。《花样年华》是九七回归后的香港人对60年代香港的回忆,而在60年代的香港时空中,“对倒”着的是对老上海的记忆。60年代的香港,有着很典型的殖民文化氛围。《花样年华》在精心营构的时空里,借助各种的电影元素,真实反映了60年代拥挤不堪的香港城市景观,以及这个时代香港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状况。影片借一段注定要流散的情缘,讲述了一个60年代上海人在香港的故事。这既是关于爱情的,是纯属个人的、私密的记忆,又是关于香港的,是特定时代、特定城市的记忆。影片在王家卫惯用的叙事机巧和特异的时空构筑中,把二者结合起来,以情感故事为载体,在个人化的体验表达和两难的情感处境中,真实展现60年代香港文化身份的两难,表达“香港经验”中的困惑、彷徨、无所适从。透过情感的叙说、生活的日常风貌,、社会和文化困境进行了思考,试图从和传统、中国内地、历史的多种关系中界定香港的身份,完成一种文化的追寻和体认。
从表面上看,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婚外情的故事。苏丽珍和周慕云同一天搬家,成为邻居,因发现各自的伴侣有私情,互诉衷肠而渐生情愫。然而,他们最后没有逾越传统的社会道德规范,把60年代的一段爱情故事尘封在记忆里。王家卫在《花样年华》中把爱情推到了故事的前台,在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变化中讲述了一段“发乎情止乎理”的情感故事。尽管预设了复杂的人物关系,但王家卫没有把这个故事安排成婚外情的错杂纠葛。张先生(苏丽珍丈夫)和周太太(周慕云妻子)、何太太和徐小姐的形象在影片中只不过是背景的交代,是身份迷失的“缺席的在场者”。影片重在表现苏丽珍、周慕云的挣扎两难的情感体验,以及在情感游戏中的人物身份的困惑。苏丽珍和周慕云、张先生和周太太、何先生和徐小姐的三组人物关系,是婚姻出轨故事的三段情感轨迹,也是人物身份迷失的过去和将来。影片在展开故事的过程中,有意删繁就简,虚化了情感的实质性,仅以一些细节提示情感的发展。张先生和周太太、何先生和徐小姐的情感故事,成为了苏丽珍和周慕云的背景和镜像。
影片以几段“戏中戏”简洁勾勒苏丽珍和周慕云的情感故事。因为发现各自伴侣的私情,苏丽珍和周慕云开始接近,两人第一次约会谈论的是背叛。在以后的约会中两人总想通过对各自伴侣偷情细节的揣测和模仿,来穷究私情滋生的根源,却不能阻止自己心中情感的渐生渐长。影片通过三次模拟游戏,表示两人关系的变化。第一次是在首次约会之后,他们揣测和模仿另一对情人的开始,其实也是他们自己的开始,虚虚实实让人颇费猜疑。第二次是排演如何向张先生追问婚外情的事,暗示了他们之间悄无声息滋长的爱情,而苏丽珍的伤心是她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无法选择的伤心,是预先知道无法把握这一段浮世情缘的伤心。第三次是预演分手一幕,亦真亦假。其实这种模拟游戏慢慢就成为他们情感交流的私人语言。试探接近——恋情滋长——结束情缘,全部交代在三段模拟游戏里,这是本片表达爱情的一种比较新颖别致的方式。爱情故事本身是普通的,但这样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别致的。模拟游戏是一个预设的结局,它明确规定了观众的心理准备,不是去期待一个戏剧性的婚外情故事,而是去体会王家卫电影中始终存在的孤独感和漂泊感。
影片借助了一系列重复的情节元素,精心营造一种情绪情调,把这段没有结果的感情纠葛表达得淋漓尽致。这些情节元素在王家卫的电影中经常可以看到,诸如镜子、栅栏(或者鸟笼)、绣花拖鞋、公用电话、时钟等等。这些情节元素经过精心编织,和王家卫在镜头运动和画面构造方面的刻意经营一起营造出浓浓的怀旧情调,十分贴切表现了一份过往岁月的爱情幻象和失落情怀。在王家卫的电影里,无论是在空旷遥远的沙漠,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还是在喧嚣拥挤的香港,我们都能深深领略到情感流离无根的惆怅之情。无论故事怎么编排,时空怎么改变,那种追怀感伤始终存在。
情感的孤独和漂泊,是王家卫电影中贯穿始终的主题。或者是无父无母的身份,或者是爱情的求而不得,人物的焦虑与困惑、迷失与寻找,表现出香港人对自己文化身份的纠结以及对于未来的迷茫不安。因为无根,所以要去寻根;因为身份的错乱与迷失,所以要去追寻文化、身份的一致性。香港由长期经验积淀下来的身份危机由于历史的变化而凸现、扩散出来,80年代以来大量的香港影片,都把香港/大陆的关系作为编织情节、设置冲突和编排人物的支点,关锦鹏的《阮玲玉》是其中翘楚。在新的历史时期,香港无可回避地面临文化何去何从的选择。王家卫把他的思考设置为人物关系,进行隐喻性表述,表现了“香港经验”中那种身不由己和两难的处境。苏丽珍与张先生与周慕云,周慕云与周太太与苏丽珍,何先生与何太太与徐小姐。这些人物关系纠缠不清,紊乱如麻。何先生在何太太与徐小姐之间左右逢源,似乎游刃有余,但是,他的困扰在苏丽珍代为转达的电话托辞背后可以猜想。影片没有表现何先生面对选择的挣扎困惑,只是他将不断地视场合不同而选择他的两条领带。而在张先生/苏丽珍、周慕云/周太太四个人中,张先生和周太太各自背叛了自己的婚姻,但他们的私情没有结局,身份无法确定。周慕云对情感的追寻注定是没有回应的,他只有远走南洋,在记忆与逃避之间忍受心灵的折磨。苏丽珍夹在两个男人之间,无助伤心、无从选择,只能孤独守着过去任凭岁月慢慢老去。影片以这些人物相互错杂的关系传达了“香港经验”中的困惑、彷徨和无所适从,人物身份的艰难定位,是香港的身份复杂不明、文化上无处依傍的生存困境的一种表白。《花样年华》中人物的两难情感选择和身份上的不明不白,表征着香港尴尬的文化身份处境。这是处在历史夹缝中的香港,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的疑惑。
《花样年华》在空间形态和表现形式上没有用完整的画面构图,到处是拥挤的,办公室是拥挤的,楼道是拥挤的,居所也是拥挤的。这种空间形态是王家卫电影中常见的,拥挤、喧嚣、封闭、孤独,是地窄人稠的香港城市特征。影片刻意而不留痕迹地展现斑驳狭窄的楼道,明暗分明的小巷,局促狭小的房间,构建了60年代香港的城市影像。这种空间特征,强调了60年代香港社会环境氛围的无形压力:60年代的婚姻道德观念,华人世界里常见的飞短流长,苏丽珍的出入进退都在房东邻居的有意无意的“监视”之中。而且强调了男女主人公的心灵不自由,两人之间“我们和他们不一样”的自我期许和道德约定注定了他们要选择逃避和出走。与此相应的,影片在技巧方面也强化了这种空间特征。影片大量采用固定的机位和中近景的镜头,摄影机的前面总是设置许多障碍,或是在走廊的后面,或通过各式门框、窗框、巷口,或通过镜中的虚像,画面总是被阻挡被疏离的,隐喻着周围环境和个人心灵的封闭和不自由。
“60年代的香港,大陆去了很多人,一个小楼中可以住很多家不同的人,有很多的邻居。今天我们可能不太知道住在公寓旁边的那户是谁,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彼此知道。所以我想,那个感觉是我要在电影里把握的。这个故事是两个人的故事,应该是个悬疑的电影,就是很多事情都不是在镜头前面发生的,你要猜的。这个摄影机就好像其中一个邻居,偷窥他们两个人在做什么。所以,基本上摄影机都是在走廊的后面啊,或者在某个前景挡住一点,这是我们拍时想做的事情。”【3】在游离阻隔的摄影技巧中,《花样年华》的场景空间有明确的区分。公寓楼里的公共客厅和厨房、楼道、工作场所,是作为处于他人窥视之中的公共空间而构建的。这些空间拥挤逼仄、人来人往交错而过,到处是门窗,摄影机的机位总是置于门窗之外,从外往里窥探观看。电话机、打字机是公共空间的元素,人与人之间的寒暄打探不断重复。在公共空间里,苏丽珍和周慕云在他人的眼光中,小心翼翼地“发乎情止乎礼”。
作为一种空间区分,影片有意将卧室、宾馆房间界定为一种私人空间,摄影机往往进入空间内部,强调一种私密性。在这些空间场景中,苏丽珍和周慕云单独相处,一起写武侠小说,纵容内心情感的滋长。鲜艳的红色成为浓烈的情感的寓示:红色的床单、红色的窗帘、红色的旗袍和外套等。私人空间设计了大量的镜子、台灯等元素,迷离的光影、重叠的空间,和流动的摄影一起营造出惆怅感伤的情绪,让观众体味着爱情的无可抗拒和无所适从。
在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之外,影片还着意展现了一个空巷,是苏丽珍和周慕云模拟各自伴侣出轨的戏剧空间,陈旧斑驳的窗户铁栏杆始终存在于前后景,将空间形态分割,人物内心的束缚和不自由展露无遗。
这些空间设置和独特的影像细节,营造了影片故事的无奈喟叹情绪。缓慢的节奏,大量内景和非自然光效,使画面呈现一种阴暗朦胧的氛围,看着周围的世界像隔着一层布满灰尘的玻璃,动静之间总有恍如隔世之感,弥漫着无痕的落寞。不断反复出现的行走楼道的镜头,或是苏丽珍独行,或是两人交错而过,都是采用高速摄影,悠缓的慢动作配合爵士风格的背景音乐,强化着那股莫名的惆怅。因为这是一段60年代的往事,在导演精心营造的怀旧、浪漫的情调中,每个人都能闻到一缕岁月久陈的熏香。然而,这个故事又远远超越了爱情,我们总能在影片中接收到爱情之外的信息。潜入《花样年华》的影像深处,依然可以找到王家卫对彷徨、困惑、迷失的香港经验的表达。这在王家卫的电影中似乎是一脉相承的。流离无定的情感经历、嘈杂逼仄的空间展示、强烈的时间感、注定失败的宿命感等一系列反复隐现的叙事动机,对应着香港民众面对“九七”的复杂心路历程。
在这部影片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女主人公所穿的一袭袭花色各异的高领旗袍。加上爵士风格的音乐,一个时代的缩影就慢慢呈露出来。在电影的叙事层面,这些变化多姿的高领旗袍不仅传达出苏丽珍在道德上的束缚和节制,更重要的是时空叙事的需要。旗袍的更换表达了时间的流动,借以分辨空间的不同。影片以苏丽珍旗袍的变化,把记忆中的一枚枚日子区分开来,使影片的叙事具有日记式的灵活、跳跃。以旗袍为时间性线索,就会发现影片的时空并非完全随意和错乱无章,其中的省略和剪切都是有章可循的。影片中表现芝麻糊的细节一共用了三组镜头:前一组镜头是在过道上,阿炳与苏丽珍随意闲聊,告诉她周慕云生病、想吃芝麻糊,下一组镜头就是苏丽珍熬芝麻糊,但人物的着装有变化,其实就暗示了时间的流逝。紧接其后的是周慕云向苏丽珍道谢,服装又不同。这三组镜头并不是一天之内的,只是在这些日子里,烙印在记忆深处的就是关于芝麻糊的细节,这一部分记忆因此得以凸显,多个日子就以此为点串接起来,其它的都被淡忘或忽略。如果仅把苏丽珍的旗袍看作眩目的视觉感受,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遗失影片的叙事内涵。王家卫电影中的人物对时间的感受总是异常强烈,而记忆中的时间概念的长与短,是与某些细节紧密相联的,与物理意义上的时间长短完全不同。《花样年华》中,有时虽然只有短短的、连续性很强的几个镜头,时间跨度却很大;有时上下两组镜头很长并且貌似断裂,但敷演的仍是原时原地的经历。这种时间感的刻意经营,以旗袍来使之明晰、有迹可寻,使我们观看《花样年华》就象翻开一本发黄的日记,其中零碎记载的往昔生活,都是让人感怀至深的,时间的长短是由感触的深浅、记忆的深浅决定的,观看的体验与主人公的个人生存体验形成了同构关系。直接借助于旗袍的更换表达时间的更替,使电影语言的组织更为简洁,叙述更为干净利落。
(同一个“约会”吃牛排场景,旗袍不同暗示时间不同)
而在“香港经验”的叙述层面,旗袍是一种怀旧文化和香港身份的确定。60年代的香港,有许多大陆移民,其中尤以来自上海的为多,香港电影中的上海影像往往是身着旗袍的女性身姿。苏丽珍每次出场都穿着高领旗袍,这是人物的性格象征,代表了中国传统女性的温顺和矜持;也是60年代的时代象征,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流行”服饰,这些美丽的旗袍是2000年的王家卫对60年代香港的记忆,同时也是60年代的香港人对大陆的记忆。隔着时间的长河观看,就弥漫上一股怀旧的情调。而怀旧感、失落感是九七前后探讨香港人集体心态、香港经验的电影的共同基调,《花样年华》也不例外。“影片中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不单单只是一个我们虚构的爱情故事,还是一个关于过去的、时代的故事。”【4】《花样年华》本来是一个跨越60年代至90年代的城市故事,王家卫拍到60年代时突然很怀旧,于是90年代就不见了。舍弃了90年代的故事就是为了更好地营造怀旧的氛围,便于直接地在时间/历史的向度上进行追溯,寻找中国文化的往昔烙印和深层结构。典雅多姿的高领旗袍是充满象征和隐喻意味的文化话语,标识了香港的文化从属地位,香港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不可割裂的关系。影片自始至终,苏丽珍总是穿一件花色相异的旗袍,在王家卫的电影中,这是一次比较明显的文化体认,是站在现代回忆60年代的香港时,对香港文化身份的追溯和确认。旗袍在本片成了最好的表述道具,承担了超越所指的文化认同功能,从而缓解香港由长期经验积淀下来的身份危机/文化危机。
60年代的香港有大量的大陆移民,因此也充斥着各种的语言/声音。这是香港城市的日常状态,也是香港经验的一种表达。《花样年华》中人物的对话主要是粤语/广东话、上海话,周慕云的朋友阿炳则说的是普通话。电影中使用的某种语言或者方言,往往指涉的是文化身份或者国族身份的建构和认同。粤语和上海话、普通话在影片中同时共存,这是香港这个移民城市的历史经验。
影片通过上海话确定苏丽珍、孙太太等人的上海身份,确定了这是60年代上海人在香港的故事,也就确定了60年代香港的老上海情调。这是60年代香港的特有现象,这个边缘城市与上海的关系并不因地域的隔离而疏远。软语伲侬的上海话与旗袍一样是充满象征和隐喻意味的文化话语,同样隐示着60年代的香港与中国文化的根基的联系。而粤语/广东话是香港的本土文化,是香港城市的独立身份。普通话-上海话/母体文化与广东话/本土文化,以及外来文化在香港这个狭窄、拥挤的城市空间里和平共存。在本片中,外来文化虽然不是直接借某一种语言来喻示,但也是在人物的对话中间接传达出来的。苏丽珍和周慕云第一次约会,说到各自伴侣那个一模一样的包,一模一样的领带时,都强调是“在香港买不到的”,是外来文化的象征。张先生经常出差日本,周太太也从日本寄信回来。香港在空间地域上的文化共容性使香港的文化一直处于无中心、无主体的状态,在这种文化中,人们无法给自己定位。语言的多样共存恰恰就暗示着香港主体文化身份的迷失,这与影片中多种风格的音乐一样,是表现60年代香港经验的重要因素。
60年代香港的声音是纷杂的,不仅是语言,还有音乐。60年代的香港还没有电视,香港人每天都听广播。而那个时代的香港有不同的人种,听不同的音乐,什么都有。要回到和表现那个时代,音乐是不可或缺的。影片以爵士风格的音乐为主,配合着故事的渐渐深入,背景音乐插入《Yumeji’s The me》、《Aquellos Ojos Verds》、《Te Quiero Dijiste》、《Quizas Quizas quizas》、《梭罗河畔》、《花样的年华》、《双妈会》、《桑园寄子》、《四郎探母》、《红娘会张生》、《双双燕》、《情探》等。这些音乐不仅贴切地适应了影片的节奏,还建立了一个立体的影像空间。首先是香港人的记忆空间,作为60年代流行音乐代表的歌曲会敲开每个香港人的心灵,让曾经的岁月情怀慢慢被牵引回来。其次是影片故事的现实空间,与特定情境的人物心境相吻合,传达出一种感伤、哀怨和人类与生俱来的宿命。各类风格、不同语种的音乐共存于同一部影片中,既表明香港的殖民经验,也能让人看到香港与中国文化丝丝缕缕的底蕴相连。音乐与语言一起构成香港经验中的声音部分,纷纷杂杂又相融相谐,香港就只能在这其中寻找出各种碎片,拼凑出自己的身份。
注释:
1.李焯桃:《香港电影与社会变迁》,转引自张英进:《香港电影中的“跨地区想象”:文化、身份、工业问题》,《当代电影》2004年第4期。
2. “对倒”是邮票学的专有名词,指一正一倒的双连邮票。在小说《对倒》和电影《花样年华》中,延伸为一种平行对应的叙事。
3.张会军《与王家卫谈〈花样年华〉》,《电影艺术》2001年第1期。
4. 张会军《与王家卫谈〈花样年华〉》,《电影艺术》2001年第1期。
《细读》约稿启事
1、来稿请写明作者真实姓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邮箱,并附作者简介,注明工作单位、职称、学位、主要研究方向。
2、稿件要求原创,请勿一稿两投。一经发表,即付薄酬。
3、若文章配有图片,须保证所用图片不会引起版权纠纷。
4、文章注释请用脚注,每页重新编号。
5、来稿请投:fujianshidaxidu@163.com
主编:涂秀虹 陈 芳
策划:郑家建 葛桂录 余岱宗
郭洪雷 陈 芳 涂秀虹
本期编辑:黄育聪 郑效莹
图片: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