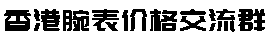子牙按:很抱歉“消失”这么长时间,因为工作关系,我每个月都要到海外一段时间,期间日夜颠倒,完全无暇他顾,所以上期讨论的议题,到今天才能奉上下篇,实在非常抱歉。不过,因为正好这次经停香港,也让我透过再一次的实地调研,可以给出更准确的答案。
畸形发展的香港地产被广泛认为是“香港之癌”,它不仅放大了香港的贫富差距,透支了市民消费能力,还瓦解着城市发展的伦理价值,给香港市民,特别是中下层市民,带来了难以名状的切肤之痛,成为一系列尖锐矛盾的根源之一。
那么,是什么让香港产生了这个癌痛,大致又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找到病根。
第一个首要病根是香港的土地供应制度。香港无论是港英政府还是回归后的特区政府,都受惠于房地产业。港英政府时,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为了让货品能够廉价销往海外,在全球需要大量自由港口,身为殖民地的香港,因此被宗主国英国定位为自由贸易港。
此举导致港英政府无法从贸易中征税,加上香港缺乏自然资源,港英政府唯一可做的便是掌控土地,搞大家现在都很熟悉的“土地财政”。这就使得港府成为香港土地的唯一供应者,最大的土地开发商,透过限量卖地抬高地价,逐年成为历届港府最倚重的财政来源。
这一情况在中英谈判时又被人为加剧。香港回归谈判时,为防止港英政府寅吃卯粮,,《中英联合声明》限定港英政府在回归前每年只能售地50公顷,土地供应因此被大幅压缩,导致房屋价格在80年代快速上涨,在回归前达到最高点。
港府从1999年开始施行的“勾地”政策,也是推高香港房地产价格的罪魁祸首。因为香港政府几乎拥有香港所有土地控制权,能起到限制土地供应及保障政府卖地收益的“勾地”政策,使得发展商只能以信息不对等的出价方式,来向政府表明购买意向,在地产商和政府的不对称博弈过程中,唯一不变的结果就是地价不断上涨。
而港府则从中赚得盆满钵盈。统计显示,从2009到2014年,港府平均每个财政年度的总收入中,有高达24%来自卖地、补地价、物业税和印花税等地产相关项目。
也是循着这个思路,香港土地规划对地产开发进行了严格限制。香港总共约1111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按照用途,住宅面积合计仅77平方公里,占到香港总土地面积的6.9%,其中私人住宅、公营房屋和乡郊居所分别为26、16、35平方公里。其它大量为不可开发的林地、草地、灌木丛林。甚至农地也占到了4.6%。
而我们知道,香港农产品基本都依赖进口,农地基本上没有产出价值,大多变成了使用效率极低的工业堆场。而这些农地,其实完全可以拿出来一部分进行政府公屋或商业地产开发。
这一点香港和内地不同,内地有超过13亿人,如果饭碗被端在其它国家手里,粮食供应万一出现问题,那麻烦可就大了,到时候别说被人卡住脖子勒索,连进口可能都没处进口。,所以香港可以不要农地,内地绝不可以机械照搬,农业用地要能保持粮食基本自足,这一点对内地非常重要。
之前内地搞房地产市场,包括土地财政,几乎都是全盘照端从香港学习。内地房地产市场这些年迅速发展,制度引进居功至伟。但与此同时,这种不加选择的引进,也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类似于香港的问题。以后再搞制度引进与创制,一定要结合内地实际才行。
香港癌痛的第二个原因,是地产商和银行等地产金融业的绑架。
香港居民的住房花销占总收入的30%以上,在香港素有“楼市好,经济好”一说,但其实地产本身在香港GDP中占的比例并不高,居多维整理统计,就算在上世纪楼市辉煌的八九十年代,也不过是10%左右。
以10%的GDP,却拿走港人总收入的30%,除了作为最大地产商的港府获利丰厚,地产商利润当然也极为可观,其利润远超其他行业,单是四大地产商的税前溢利,就合计共达千亿港元。
丰厚的利润诱使资金源源不断流向地产,使得香港经济不断脱实向虚,加剧了产业畸形,其它产业发展被严重抑制。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3年,香港FDI(外来直接投资)合计为3.3万亿港元,其中与房地产相关的金额占到65%,而在2010至2012年的高峰期,更是超过80%。
另外,数据也显示,2009年,在10.6万亿港元的总贷款额中,和房地产相关的住宅买卖、建造业及物业发展共占到48%,而同期贸易融资、财务金融及批零总贷款额度合计仅有19%。2014年20万亿的银行总贷款额中,地产业相关贷款仍然超过40%。
扭曲的物业借贷,堆积出破纪录的成交额。在2009年至2014年间,香港楼宇买卖的合约总值高达3.5万亿港元,而作为国际购物中心,同期零售业销售总额却只有2.4万亿港元。
此外,从土地储备看,香港几大地产商的土地储备,加上所收购的农地,多达1010公顷,而政府拥有的土地储备却只有200公顷。地产商拿到土地后根本不急于开发,而是囤积居奇,严格控制市场供应,如政府卖地一般推高市场价格,也成为推动房价上涨的另一重要原因。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经济扭曲。一方面,港府以严格的、类似于计划经济的方式高价炒地供地;另一方面,对房地产和金融这两个具有高度垄断性特质的行业,却采取了几乎放任不管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使得后者在一个典型的卖方市场可以随心所欲。
这就使得整个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在港府卖地扒去一层之后,又被自由竞争且高度垄断的地产和金融机构联手再扒去第二层皮。层层盘剥之下,香港房价想不上涨,几乎已没有可能。这种情况,在内地这些年是不是也很熟悉?
当然,这种情况在香港尤甚,造成的产业扭曲也更厉害。因为房地产是个很长的产业链条,在内地就算价格暴涨,也能带动包括基建材料、工业制成品在内的很多产业发展,创造就业和财政税收。而因为香港几乎没有本地基建用品供应,工业制造也早已被转移到内地,这一畸形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甚。
香港癌痛的第三个原因,是有产者囿于自身狭隘利益的短视。
上述香港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的状况,以及造成问题产生的原因港府知不知道?当然知道的一清二楚。
但问题是,不仅卖地上瘾的港府自身难以从现有的利益结构中抽身,地产商、金融业者和有产阶级的政策绑架以及游说施压,也使得港府根本抵抗不了这些产业财阀的压力。
在房地产市场,港府一旦想有介入市场调控的动作,大地产商和银行等机构的杯葛、有产者破坏自由市场机制的指责即纷至沓来。而这些指责,在奉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理念的香港,,因而给港府政策创制与推行,。
我们知道,房地产行业因为捆绑了银行信贷、经济成长指标等,具有内在刚性,几乎只能上涨不能下跌,短期内房屋价格快速下跌,不仅可能引发断供潮,导致金融行业崩盘,还会严重影响到有产者的生活和资产数量,。
香港回归后第一任港府为了压低楼价,原本推出了“八万五”政策,即每年私人楼宇单位、居者有其屋单位和夹心阶层住房计划单位供应不少于八万五千个,希望十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由六年半缩短至三年。
结果,这一很有魄力的德政政策,因为生不逢时地遇到了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房屋价格在五年内下跌将近七成,引发了银行和有产者的强烈反弹,其招致的后果,关注香港时事者应该都很清楚。
因为反弹严重,港府只能停止这一政策,转而又开始卖地热楼。从此之后,历任港府都没有再敢在楼市动手。相反,为了挽救低迷的经济,港府不仅未选择发展商业和工业,反而却采用抑止拍卖土地的方式,人为提高土地价格,使得房地产日益成为香港不可承受的民生癌痛。
香港癌痛的第四个原因,和香港在国际和区域的地位密不可分。
香港是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自由港,美食中心,国际金融和区域交通中心,资金进出方便,专业人才数量极多。再加上香港背靠内地腹地,进出内地方便却因为和内地制度不同而具有充分的自由表达空间,相对于内地城市对国际社会仍具有极大吸引力,不少域外国家的官商达人,都愿意在香港置产。
这些年中国内地经济蓬勃发展,产生了一大批富人,这些富人也大多会锁定香港作为走出国门的第一步。而内地一二线中心城市这些年房价暴涨,和香港的房价差距在迅速缩小,很多人为生意、居住或投资需要,也会在香港购房,特别是高端房产,这就更推高了香港房价。
事实上,最简单地判断一个经济体(或主要城市)的未来房价会上涨还是下跌,只要看两个因素就可以:人口和资金。如果人口持续增加,资金能够持续进入,基本上房价都会维持上涨态势;反之,若人口和资金稳定不变或出现下滑,房价也会维持相应态势。
为防止外地人购房炒高房价,港府也采取了不同税收政策。比如,从2016年11月5日起,全面提高印花税率,税率统一调高至交易额的15%,使得非香港永久居民在港置业缴的税率将达房价30%。但买房多交税这种事,对那些计划在香港置产的富豪官商来说,真的没有太大作用。
上期相关阅读:《这是个天才的创意,却折射出香港难以启齿的癌痛(图)》
长按二维码,关注本公众号“杭子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