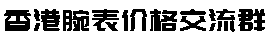
2020-09-26 12:11:00
—— 这 是 小 怪 兽 的 第 24 颗 星 星 ——
无 边 宇 宙 当 中 ,我 收 集 故 事 和 奇 迹
贼行 · 青龙背
文 | 猎衣扬
医院的楼道里,弥漫着浓浓的消毒水味。我沿着曲折的楼梯走上了二楼,推开了北数第二间病房的木门,两颊深陷的白四叔躺在病床上,气若游丝,我抬眼向天花板上瞟了瞟,努力不让眼眶里的泪水落下来……
“四叔……”我走到窗前,握住了白四叔的手。
“馋狗,你来了?”白四叔眨了眨干涩的眼皮,掌心缓缓摊开,露出了一方浸着体温的玉佩,通体如墨,形貌古拙,上面铁画银钩的铸了四个篆字。
故事要从十五年前说起……
壹
我叫毛建军,小时候上网吧天天包宿,小学没毕业,就高度近视。一摘了眼镜,三米之外男女不分、六亲不认,眯着个小眼睛,活似街上扒食的野狗,故而得了这个馋狗的外号。
我爸没工作,守着三间平房,当了个收租的房东。
我们爷俩住当中,左边那间租给了一个蹬板车的苦力,右面那间租给了白四叔。
白四叔租房子的时候,已经快六十了,按理来说,我爸都该叫他一声叔的,但两个人却莫名其妙的论成了平辈,尽管我爸不说为啥,但我也知道缘由。
只因为白四叔蹲过二十年大狱,我爸心里多少有些瞧不上他!
白四叔好洁,一身笔挺的中山装浆洗得隐隐发白,接人待物,既客气,又体面。
我童年里最好的玩伴是大壮,他爸老徐,就是那个蹬板车的苦力。老徐很辛苦,早出晚归,我爸好喝酒,终日神魂颠倒。
在我和大壮的记忆里,陪伴我们最多的就是这位白四叔了。四叔的嘴里永远有讲不完的故事,江湖传说,奇闻异事,桩桩件件都是那么的有声有色,勾得你腮帮子痒痒……
记得那年冬天的一日,农历恰好是正月初八。
大壮这一年没少帮他爸推车,他爸一咬牙,给他买了一块电子表。
搁在十几年前,这绝对是个稀罕玩意儿!
我和大壮去野湖上放了一天的爬犁,回来的时候坐了一趟公交车,下车了大壮才发现,手腕上的电子表不见了!
我们两个扔了爬犁,甩着鼻涕抽泣着在公交车后面跟着跑了二里多地,累得瘫在雪地里直抹眼泪,直到遇到了骑自行车路过的白四叔。
白四叔问了我们俩事情的经过,沉默了很久,缓缓的叹了口气,将大壮抱到自行车后座上,将我背在肩上,一步一步地向家走去。
路上,我仿佛听到了四叔喃喃自语的说了一句:
“好个贼行,怎地没落如斯……”
第二天,四叔带着我和大壮,在天刚擦黑的时候坐上了那趟公交车。
车里头灯暗人多,四叔坐在后排,微闭着眼睛,一路无言。
眼看就要到了终点站——毛纺大院,四叔突然“嚯”地一声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向后门走去,车行得颠簸,四叔的脚步有些踉跄,不小心踩到了一个老太太的脚,又撞到了一个扛行李的民工的腰,在一片嗔怪声中,四叔拽了我们两个小孩儿挤下了车,一展肩膀将我两个夹到了肋下,大踏步的向灯影暗处走去。
灯光越来越暗,毛纺大院巷子里的路曲折而幽深,四叔越行越快,有若一头在雪中奔行的虎豹,以至于雪地之上,四叔两腿的倒影都连成了一条直线!
突然!四叔收住了脚步,将我们两个放在了墙角,扭过身去,沉声说道:
“要是实在跑不动了,就出来见个亮儿吧!”
话音未落,打阴影里闪出了一个高瘦的汉子,喘着粗气缓缓地走到了四叔的身前,摸了摸自己的腰下,又翻了翻怀里的内兜,倒嘶了一口冷气,嘬着腮帮子说道:
“朋友,你这么扒活儿,怕是不合规矩吧!”
白四叔将腰杆立的笔直,沉声说道:
“好!既然你和我讲规矩,那咱们就好好聊聊规矩!贼行有三取三不取:不义可取,官商可取,窝赃可取;老弱不取,救命不取,穷人不取。今日,我眼睁睁看你取了那老太太腕上的金镯和那民工兜里的钞票!这老弱不取的规矩,入门的时候,你师父没教过你吗?”
那干瘦的汉子一声嗤笑,甩了甩一兜,冷着脸说道:
“所以,你从我身上把钱和镯子偷走,又还了去?”
白四叔深吸了一口气,咬着后槽牙说道:
“年轻人!我是在教你,江湖不是这么混的!”
“呸!老棺材瓤子,爷我怎么混江湖,用得着你教?爷想偷谁偷谁,爱偷谁偷谁!你算刮的哪路妖风啊?闲事管到老子头上了!跟你说,两条路,要么把兜里钱留下,领着这俩小犊子滚蛋,要么留下一根手筋,全做你扒活的教训!”
话音刚落,那高瘦汉子的三指一竖,两道幽蓝色的冷光一闪而没!
他手里夹了刀片!
白四叔抽动了一下嘴角,缓缓的向前进了一步,低声说道:
“既然如此,过过水(搭手过招)吧!”
那高瘦汉子诧异地瞥了一眼白四叔空无一物的指缝,随即一脸狐疑地将两只手慢慢前伸。
四只手腕缓缓地交叠在了一起。
蓦地,平地里一阵风来,卷起一蓬积雪,两个人猛地动了起来!
勾腕,引指,压肘,扎肋,封眼,搓喉……
一触即分,两人各自向前窜了一步,背对而立。
白四叔眉毛一挑,也不回身,只是缓缓地将右手向身后一探,掌心张开……
“啪嗒——”
一块电子表从那高瘦汉子的腕子上掉了下来,正好落在了白四叔的掌心!
白四叔一张嘴,将舌尖上的一块刀片卷入口中,徐徐说道:
“诫规如铁!别怪我!”
那高瘦汉子的胸腔一阵剧烈的起伏,一晃脑袋,甩了甩头上的冷汗,颤抖着嗓子说道:
“敢问……老元良,哪路开香(老前辈,是哪路英雄)?”
白四叔哈了一口气,擦了擦表盘上几滴若有若无的血点子,俯身系在了大壮的腕上,幽幽说道:
“江湖南北,掌青龙背;水火春秋,刀插两肋!”
那高瘦汉子闻言脚底下一软,扶着墙打了个晃儿,一个躬鞠到了脚面上,三步并两步的消失在了巷子深处!
贰
后来我才知道,贼行有行规:鱼禽称龙,走兽曰虎,春秋有两祭,南北贼众齐聚,所尊者有四:天、地、诫、魁。
诫是三取三不取的规矩,魁是统领贼众的贼王,宴上有青鱼,居中为大,鱼头祭天,鱼尾敬地,鱼背奉贼王,鱼腹由贼众分而食之。
故而,掌青龙背,成为了贼王的代称!
1948年,南北大贼齐聚津门赌斗。时年二十一岁的白四叔技压群雄,被推选为贼王!
听四叔说,这选贼王的场面唤做——青龙宴,群贼分金斗宝,谁盗来的宝物最贵重,便说明谁的盗术最高超。彼时贼门鼎盛,高手迭出,有人掘开了黄陵,盗来了压皇棺的如意;有人飞檐走壁潜入了帅府,窃走了大帅的配枪;有人入水爬船,摸上了英吉利的货轮,偷走了船长的钻石怀表,各方人物,手段无穷……唯有白四叔两手空空,袖在兜中,宴未开席,便将这些老贼藏在身上那些个盗来的宝贝偷了个七七八八,众贼晓得厉害,更有见识卓著的老贼看出四叔的手法似乎是大盗许灯黑的秘传——苏秦背剑!于是众人合议,公推白四叔为南北贼王。
解放后,白四叔隐匿于市井,做了一名普通的车间工人。
1983年,全国严打,白四叔做过贼王的案底子被人咬了出来,四叔被扔进大狱,一蹲就是二十年……
风急雪骤,白四叔关紧了门窗,在土炕的火洞子里焐了两块土豆,给我和大壮剥了皮,看着我们俩一边吹气一边狼吞虎咽的往嘴里塞!
吃着吃着,大壮突然抬起了脑袋,看着白四叔问道:
“四叔,你手指缝里的刀片一共在他的腕子上划了三刀,你是挑了他的手筋么?”
大壮的话一出口,四叔猛地愣住了,只见他缓缓放下了手里的水杯,皱着眉头看着大壮问道:
“大壮,你……看到我的手是咋动的了?”
大壮咽了一口嘴里的东西,打桌上捞起了一根筷子,笨拙而生硬的瞄着我的手腕一顿乱比划,随即摇了摇头,慢慢说道:
“最后一下,我想不起来了,不过要是四叔你肯教我,我应该能模仿个大概……”
白四叔将手里的水杯放在桌上,两眼直直地盯着大壮,一脸严肃地问道:
“大壮,四叔这本事,你真愿意学?”
“我愿意学!”大壮举手喊道。
我放下了手里的土豆,也举起了手,大声喊道:
“四叔,我也学!我也想学!”
四叔摸了摸我的脑袋,敲了敲我的眼镜片,笑着说道:
“馋狗,你这眼神儿不行,四叔的本事,你学不了,但是大壮可以……祖师爷,贼行不绝啊……”
从那以后,大壮就成了四叔的徒弟。白天和我一起上学,晚上到四叔的院子里学盗术,没日没夜的练翻墙越脊、探囊取物,开锁撬门,我则在一旁坐着,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热闹。
大壮的盗术学得好,书却读得一窍不通,初中没毕业就辍了学,跟他爸入了同一门行当——蹬大板车!大壮生性粗豪,下手狠辣,再加上师承白四叔,眼界更是高的没边,四叔老来得徒,一身艺业恨不得掰开了,揉碎了喂与大壮。大壮艺成之后,方圆十里的小贼没有一个敢抬头看他。索性大壮孝顺,照料四叔尽心竭力,故而四叔虽知他在外面不少交朋好友、招灾惹祸,却始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曾重罚。
高考那几个月,我忙得厉害,一直没功夫去四叔那院玩儿,直到暑假的一天……
这几年,四叔老得快极了,脑袋上的头发白的晃眼。早年烟酒不忌,寒暑不避,老了老了,咳得一天比一天厉害,三天两头地去医院报道。
我依稀记得,那是一个微冷的早晨,我拎着两箱牛奶推开了四叔的院门。
“啪——”一声清脆的鞭子响伴随着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从屋内传来,我扔下了手里的奶箱子,趴在窗户上探头一看,只见大壮正赤裸着膀子跪在屋子当中,满脸通红的白四叔拎着一根蘸了水的牛皮鞭子劈头盖脸的对着大壮一顿乱抽!
我吓了一跳,连忙推门蹿了进去,一把抱住了白四叔,急声喊道:
“四叔,您这干嘛啊?有事咱都好商量啊!”
“咳——咳……”四叔咳得厉害,腹腔鼓动得好似一架漏气的风箱。
“馋狗,你……你先出去!这不关你的事,错了就要罚,挨打你得认!说!你知错了没有……”四叔拍着桌子,指着大壮放声喊道。
“我没有!”大壮猛地回过身来,两只红通通的眼眶里闪动着愤恨和倔强的光!
我扶着四叔坐在椅子上,伸手去拉跪在地上的大壮,小声说道:
“大壮,你就认个错,又能咋的……”
“我没错!为啥要认!”大壮一甩膀子,挣开了我。
四叔咬了咬牙,猛地站了起来,一脚踹开了房门,将桌上满满的两兜子药片、胶囊、冲剂一股脑的扔出了门外!
“老子就是咳死!也不吃这些个偷来的东西!咳——咳……”
大壮抹了一把眼眶,咬着牙喊道:
“不吃药,病咋好?我蹬一个月的板车,都不够你吃一个疗程……”
“老子教你本事,不是让你去偷药铺的!那是救人的地方,救命不取啊!三不取的规矩,你都学到狗身上了?”四叔将桌子拍的震天响。
“你教我贼的本事,却不让我干贼的买卖?这不能偷,那不能偷。你不让我偷,你自己呢?南北贼王,掌青龙背!你又偷了多少?”大壮猛地站起身来,盯着四叔喊道。
“啪——”
四叔抬手给了大壮一个嘴巴。
“你破了规矩,信不信我挑了你的手筋!”
四叔话一出口,随即愣在了原地,右手颤抖着向后倒去,我连忙扶住了四叔。
“就……跪……跪在这儿!没我的允许,不准起……起来!”四叔牙缝里吐出了一句话。
大壮一转身,重重地跪了下去。
当晚,我犹在梦中,大壮不知何时,已立在了床头。
“大壮……”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
“嘘!馋狗,我要走了……”大壮将一沓钱放在了我的枕头底下。
“你去哪啊?四叔知道么?”我挣扎要起身,却被大壮一把按住。
“去哪你就别问了,我走后,我师父那儿,你勤照看着点儿,我给你留了点钱……”
我一摸枕头底下,正要把那钱拽出来,却被大壮按住了手。
“这钱是我蹬大板车挣来的,干净!馋狗,我走了,你保重!”
大壮叹了口气,一闪身,便窜出了窗子,不见了踪影。
我摸着那沓大壮留下的钱,一夜无眠。
叁
转眼间,便过了五六年的光景。
我从医科大学毕了业,在医院当了一名外科大夫,白四叔上了医保,几次大治之后,虽然渐渐地也控制住了病情,但是却性情大变,不爱说话,整日里坐在太阳底下,手捻着一块墨色的老玉,两眼无神地发着呆。神经科的郭大夫跟我说,这叫阿兹海默,但我却觉得白四叔之所以变成这样,主要是心里挂着一个人,他放不下……
农历新年,还没出正月。我从四叔家出来,走路去医院值班,路过一片毛纺大院,刚走出巷子口,便被一个人一把揽住了肩膀,我吓了一跳,扭头一看,忍不住惊声叫了出来:
“大壮!”
虽然多年不见,他长高了不少,头发短了,脸瘦了,换了一身衣裳,但我们俩从小光着屁股玩到大,我绝对认不错他!
我咧着嘴,一把抱住了大壮的脖子,狠狠地捶了两下他的后背。
“这些年你去哪了呀?”我张口问道。
大壮抿了抿嘴,拍了拍我的肩膀,打衣兜里摸出了两根烟,递给我一支,我摆了摆手,他会心一笑,自顾自地点了火,嘬着烟圈,徐徐说道:
“一言难尽,别问了!我师父怎么样?病好些了么?”
“四叔的病,基本控制住了……就是……他……其实很想你!”
大壮闻言,伸手搓了搓自己的嘴角,徐徐说道:
“最后一票买卖,干完我就收手,这些年我钱也攒得差不多了,完事以后,我哪也不去了,就守在老房子里陪他养老……”
我一愣神,急忙问道:
“买卖?啥买卖?大壮,你不会是……”
大壮一声苦笑,转过身去,低声说道:
“我还会别的么……”
我正要再说,大壮已经一跃而起,蹲在了墙头,看着我,张口说道:
“我回来的事,别告诉我师父!我很快回来!”
大壮话音未落,从路边拐角突然开来了一辆奔驰轿车,车头的双闪晃了了两下,就在我一眯眼的功夫,一个剃着青茬短发的男子夹着一个精致的小皮包,走下了车,热情而熟稔地拍了拍大壮的肩膀,徐徐说道:
“壮哥,天儿太冷了,怕你着凉,赶过来接你,咱们去吃口热的!”
大壮眉头一紧,冷着脸说道:
“姓郑的,你跟踪我!”
那个夹包的男子一咧嘴,一脸冤枉地说道:
“壮哥,这话打哪说的,误会了,还没请教,这位戴眼镜的兄弟是……”那个夹包的男子带着询问的眼神向我瞥了一眼,大壮下意识地将我拉到了身后,沉着脸说道:
“他不是道上的人,跟你没关系!”
夹包的男子笑了笑,抬手从小包里捻出了一沓钞票,递到了我身前,徐徐说道:
“虽说不是一路人,但是毛大夫,你从小和大壮是兄弟,我和大壮也是兄弟,这么一论,咱们两个也是兄弟了,既然是兄弟,这钱你拿着,给咱们四叔,买点补品!”
夹包的男子将“四叔”两个字说的极重,话一出口,大壮猛地瞪圆了眼睛,胳膊一甩,“砰”地一声抽在了那男子的手上,扬手一摸,顿时在那男子的脸上开了三道血口子!
那男子还没来得反应,就被大壮扼住了喉咙,两只闪着冷光的刀片瞬间抵在了那人的眼珠子前面。
“郑卫红,查我底也就罢了,你还想动我师父!”大壮咬着牙低声吼道。
郑卫红?这个名字我太熟悉了,这几年市里最大的开发商,原来就是他!
郑卫红被大壮的神态吓了一跳,一边深呼吸,一边说道:
“兄弟,我也是为了你好,几千万的买卖,我身后还有大老板,出了闪失,咱俩谁也跑不了,兄弟不敢不谨慎啊……你好好帮我把那些东西取来,你拿钱走人,我保证老爷子平平安安!”
我闻言一愣,随即说道:
“大壮,这姓郑的不是好人,你莫要帮他!”
郑卫红冷笑着瞥了我一眼,沉声说道:
“晚了,大壮已经接了的单,是青活儿,成了拿钱,败了断手!”
我虽人不在贼行,但自小就在四叔身旁打转儿,“青活儿”我还是明白的!商行里有人遇到了麻烦,会在黑市上挂牌悬赏,一般都以木牌为记,可若是出价高到了顶,想找业内最顶尖的高手,便会挂铜牌,故称“青活儿”,接了青活儿,便等于自诩顶尖好手,故而成了翻倍,败了就得断手!
听到“青活儿”两字,大壮缓缓地松开了扼住郑卫红咽喉的那只手。
“这就对了!”郑卫红如释重负,一边弯下腰去捡散在地上的钱,一边嘀咕道:
“我说兄弟,我都打听了,那老棺材瓤子都把你打出家门了,你还理他做甚?以兄弟你的本事,完全没必要急着收手,干完这票,咱们再去南方,做几票……啊——”
大壮一把按住了郑卫红的脑袋,将他按在了车头上,手腕一抖,割下了郑卫红一只左耳,郑卫红猛地一声惨叫,栽在了地上,捂着右脸,殷红的鲜血顺着他的指缝滴落在了雪地里。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我师父是南北贼王,岂容你个奸商说三道四,滚——”
郑卫红咬了咬牙,伸手在雪地上一阵摸索,拾起了那片耳朵,转身钻进了车里,飞一般地消失在了路口。
“大壮!洗手吧,四叔不希望你……”我正要说下去,大壮突然笑着捏了捏我的肩膀,接口说道:
“是!师父不希望我再混贼行,可是我不像你,读书好,能做大夫,除了偷,我不会别的!现在已经没有大板车了,我还能做什么?现在这物价,买套房子要多少钱?买件棉袄要多少钱?馒头都涨价了啊!师父离开江湖太久了,院子外面,不是他当贼王那个世道了!钱啊!钱啊!干什么都要钱啊!师父老了,没儿女,就我一个徒弟,我得养他,我算过了,干完这票,我钱就攒的差不多了,我打算在南方买个小别墅,把师父接过去……”
话音未落,大壮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第二天一早,我和四叔坐在屋里吃早餐,四叔抽动了一下鼻翼,抬起眼来,看着我问道:
“这几天可是认识什么新朋友了么?”
我心里一沉,一脸无辜地摇了摇头,狠命地往嘴里塞了半个馒头,鼓着嘴说道:
“没……没有啊!”
四叔微微一笑,徐徐说道:
“馋狗,你是不抽烟的,医院禁烟,你能接触到烟气的机会很少,这些年你身上染过的烟味总共就那么七八种,但都不是你现在衣服上的味道!好孩子,你打小就不会撒谎,别装了,告诉四叔,是不是大壮回来了?他去找过你对不对?”
四叔缓缓地放下了手里的粥,两眼露着神光,炯炯地看着我。
我咽了一口唾沫,一咧嘴,一脸茫然地说道:
“没有,这话是哪说的?我根本没见过大壮,您肯定太想他,想出幻觉了!四叔你慢慢吃啊,我上班要迟到了,我走了啊……”
我手忙脚乱地套上了大衣,拎着包推开了门,夺路而去。
路过那片毛纺大院的时候,正看到好几台挖掘机在路边作业,一百多口子居民拎着镐把和施工队对峙在巷子口,一边叫嚷,一边相互对扔砖头瓦块。
这几年城里边到处都在改造城中村,拿地皮搞开发的开发商良莠不一,拆迁的补偿有多有少,三天两头的闹强拆。这片老平房俗称“毛纺大院”,是毛纺厂最早给职工建的住房,只有居住权,没有所有权。05毛纺厂倒闭,职工下岗安置的钱补不上,厂子和职工签了合同,将这片房子以低价直接卖给了现居住在这里的下岗职工,以此来顶替一部分安置费。去年年底,这一片被划进了改造区,负责拆迁的开发商,就是那个郑卫红,大手一挥,以这些居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为借口,非要按厂区房的低标准给付安置费,毛纺厂这些下岗的职工不干,拿出了当年厂子和自己签的合同,但是郑老板不认,把挖掘机开到巷子口,直接就开始推。居民不服气,聚众成群,一边准备着打官司,一边和拆迁队对峙。
我自幼胆小,一见这阵仗哪敢上前看热闹,扭着脑袋,飞也似地换了条路,直奔单位而去。
肆
正月初八,北风正劲。
我刚走出医院的大门,便被守在街口的白四叔一把架住了胳膊,不由分说地拖着我向南走去、
“四叔,你这是要干什么啊?”我满脸不解地问道。
“别问了!”四叔一声冷喝,打断了我的话。
我见四叔动了真怒,连忙闭上了嘴,加紧了脚步,跟着四叔一路狂奔,没过多久,就来到了毛纺大院的巷子口的一处院墙底下。
四叔松开我的胳膊,抬起头看了看天,喃喃自语道:
“盗风不盗月,盗雨不盗雪,肯定就是今晚……”
这两句话,小的时候我曾听四叔讲过,一个有经验的老贼,之所以“盗风不盗月”,乃是因为刮风天会冲淡盗贼的气味,不利于猎犬的追踪,所以要“盗风”。而月光太亮,会映出盗贼的影子,容易被护院的高手发现,所以不能“盗月”;雨水可以冲淡脚印,而积雪却最容易留下足迹,所以才有“盗雨不盗雪”的贼谚。
今夜无月无雪,却有风。
绝对是身手高明的老贼出手的好时机!
“馋狗,你就蹲在这儿!看到有人从墙头下来,你就用着棍子抡他!”四叔从一户人家后院的柴禾垛里抽了一根肘长的木头塞进了我的手里,足尖一点,两臂一伸,从墙头抽下一只土瓦,从身后掏出了随身携带的保温杯,拧开了盖子,浸湿了他买菜的布兜子,用布兜子紧紧地裹住了那只土瓦,往地上轻轻一摔,发出了一声闷响!
四叔蹲下身,将瓦上的布兜子解开,取出了那片不带一丝破损的土瓦,一个纵越,窜上了墙头,将那片土瓦再次放回了原位,从兜里摸出了一个小瓶的香油,伸出舌头,像狗一样晃了一晃,找了找风向,随即在指头上抹了一点香油,在墙头来回踱了踱步子,将手指上的那点香油轻轻的抹在了下风口一块硬币大小的地方,又从墙边抠了一把土块,握在掌心搓得粉碎,轻轻地吹在了瓦上,轻轻地一翻身,落在了平地上。
“咳……咳咳……”四叔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
我连忙上去拍了拍四叔的后背,小声说道:
“四叔,你都八十多了,别扯这闲篇儿了,咱回家涮点儿羊肉吃吧!”
四叔紧喘了好几口粗气,抬腿一脚蹬在了我的大胯上,将我踹倒在了墙角里!
“蹲好!”四叔一声低喝,转身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也不知蹲了多久,墙头上突然传来了一声瓦片碎裂的脆响。
“咦?”墙头上一个低沉的男声诧异地叹了口气,随即一道黑影从墙上翻了下来,落地时晃了一晃,才稳住身形。
我吓了一跳,拎起手里的木头便向那人抡去,那人身法极快,足尖一点便闪到了我的身侧,两手一错,便卸掉了我手里的木头,肘尖一抬,点在了我的心口,疼得我瞬间弯下了腰!
“啊——”
我心头火起,没命地抱住了那人的腰,张开大嘴,啊啊的乱叫。
“馋狗,馋狗,咋是你?”那人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抬起头扶了扶眼镜,凑到跟前一看,惊声呼道:
“我去,大壮!哎呀……漏了,四叔和我一块来得,他要堵的人,原来是你!你快走……”
我推着大壮往巷子外走,一回头正看到阴影里立着一个有些伛偻的身影!
“四……四叔?”
大壮轻轻地拨开了我的手,低声说道:
“打我踩碎那片瓦的时候,我就该想到的,除了我师父,谁又能知道这水裹布,断瓦筋的手法,又有谁能估量出我落脚的方位和步子的长短,提前在我脚尖的落处抹上香油,更能算出我重心不稳,必定下翻落脚!除了我的授业恩师,还能有谁?”
大壮咧嘴一笑,推开我,两膝着地,给四叔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
“三天前,毛纺大院,有三十二户的合同被盗,是你干的?”四叔从兜里摸出了一把锁头,扔到了大壮身前。
“我开锁的本事是您教的,自然瞒不了您,是我干的!”
四叔有些发抖,咬着牙冷声说道:
“今晚还剩最后三家,我在这墙外等,我多希望,今天等到的人,不是你!”
“师父!我……”
“我问你,三不取第三条是什么?”
大壮直起了身子,徐徐说道:
“穷苦不取!”
四叔点了点头,徐徐说道:
“难为你还记得!我再问你,贼行的规矩,破了诫,该当如何……”
“断手筋,逐出贼门!”
大壮眼睛猛地一亮,打断了四叔的话。
四叔嗫嚅了一下嘴唇,正要说话,冷不防大壮猛地站了起来,目光灼灼地看着四叔说道:
“师父,世道变了!劫富济贫,忠义肝胆,那一套老江湖的东西行不通了!如今的贼行,认的是兜里的钞票,不是您怀里那块老玉了!”
四叔愣了很久,慢慢发出了一声自嘲地苦笑:
“道不同,不相为谋!规矩是规矩,世道是世道,不能混!别管世道怎么变,坏了规矩,就得认罚!咱们爷俩儿,过过水吧!”
四叔走到了大壮的身边,两腕前伸,递到了大壮的身前。
大壮抹了一把通红的眼眶,涩声说道:
“师父!你……老了,不可能比我快!”
四叔的嘴角用力地挤出了一个微笑,故作镇定的说道:
“要么我死,否则你别想过去!”
一阵冷风席地卷来,四叔的眼神一亮,抢先动了起来!
勾腕,引指,压肘,扎肋,封眼,搓喉……
一触即分,两人各自向前窜了一步,背对而立。
寒风呜咽。
四叔没有回头,只是颤抖着手,缓缓向身后探去……
“啪嗒!”
三张牛皮文件袋捆扎的纸卷落在了四叔的掌中!
这一幕,我太熟悉了,十五年前,同样也是在片毛纺大院的小胡同里,同样的过手,同样的招法,同样的结果,只是这一切都变了!我无法分辨,究竟是这世道变了,还是我们变了,究竟是世道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世道……
“滴答!”
一滴鲜血顺着大壮的手腕滴在了雪地之上,我连忙跑到大壮身边,拎起了他的手腕。
每条腕上,两道细若发丝的伤口,交错纵横地挑开了大壮的手筋。
“四叔!你干了什么啊!”我跺着脚,哑着嗓子喊道。
“大壮你放心,我是外科医生,我手法很好的,快走,咱们去医院,我给你接上,都没事的啊……”我平端起大壮的两只手,拖着他正要往前走,却不料大壮蓦地一声轻笑,一顶肩膀,将我撞了一个踉跄。
“馋狗,不用费心了!”
“大壮?你……”我扑了扑身上的土,爬起身来。
“师父!你给的本事,我还了!”大壮猛地抬头喊了一嗓子,脚尖一点,冲进了黑暗中。
我抬腿追了两条巷子,也没跟上他的影子!
“我去……”我喘着粗气,狠狠地踹了一脚路边的垃圾桶,拖着沉重的脚步顺着来路往回走!
一抬头,看到四叔竟还一动不动的立在原地。
“他留手了,我真的没有他快……”四叔喃喃自语了一句。
我没有听清,迈了两步走到了四叔的身边,小声问道:
“四叔?你说什么?”
四叔两眉一挑,两道浊泪顺着眼眶流了下来,只见四叔僵硬地扭过头来,抽动着嘴角,哀声喊道:
“我说——贼行……绝了……啊——”
四叔一仰头,猛地咳出了一口黑血,整个人向后直挺挺的栽倒在了雪地里……
伍
凌晨四点,四叔终究没跨过那道坎儿,倒在了ICU的病床上!
当晚,我回到四叔的老屋,打院门口支了一个火盆,给四叔烧了些他随身的老衣裳和一些纸钱金箔……
黑烟呛得我直辣嗓子,连咳了好几声,我抹了把鼻涕抖开了一件月白色的中山装,四叔活着的时候,最爱穿的就是这身儿,咽气儿的时候都没有离身。
“啪嗒!”
一声脆响,打衣服兜里甩出了一块东西砸在了火盆底下,我拎着小木棍,打纸灰里扒拉出了一块掌心大小的黑玉。
正是那块四叔天天捻在掌里的玉,通体如墨,形貌古拙,上面铁画银钩地铸着四个篆字。记得前几年,大壮走后没多久,四叔天天发着楞,瞪着一双昏黄的眼球坐在树底下发呆,手里摩挲着这块玉。曾经有一次我问四叔这玉上的四个字是什么,四叔咕哝了一下嗓子,嗫嚅着嘴唇只是摇头,却不说话……
“这玉上到底刻着的是个啥?”我按捺不住心头的好奇,将玉捻在手里,擦去了上面的浮灰,揣在了上衣兜里。
第二天一早,我揣着白四叔那块黑色的古玉来到了城北的古玩街,东数第六家,是黄秃子的铺面,他老爹前年摔折了腿,就是我给治好的,我和他也算有些交情,黄秃子长年倒腾文玩,瓶瓶罐罐上的各样文字都能认个七七八八。
我绕过了柜台,拍了拍黄秃子的肩膀,将手里的古玉递了过去。
“黄老板!掌掌眼!”
黄秃子笑了笑,接过那块古玉,迎着光打量了一番,一脸亢奋的说道:
“毛大夫,您这宝贝,怕是秦汉时候的老物件儿了!看这玉质,肯定价格不菲,看着样式,不像是平常的饰物,应当是某种象征身份的信物,上面这四个字刻的是秦小篆……”
我接回了那块古玉,张口问道:“这玉上的四个字,咋念?”
黄秃子清清嗓子,用手指着古玉上的四个篆字,一字一顿的念道:
“盗、亦、有、道!”
- the end -
“
师父,世道变了!
劫富济贫,忠义肝胆,
那一套老江湖的东西行不通了!
如今的贼行,认的是兜里的钞票,
不是您怀里那块老玉了!
”
白四叔直至身死
都抱守“盗亦有道”的行规
奈何世事变迁 人心不古
唯一的徒弟双手皆废
他既无子嗣,也无高足为继
心中崇信的三取三不取
只得与一块秦汉老玉一齐入了黄土
“
畴昔之夜,盗亦有道。
当今之世,道亦有盗。
”
——木心《素履之往》
————————————————————
小 怪 兽 的 第 24 问
:
新年快乐,你有什么想对怪兽说的话?
其他的话
周二图文下,评论赞数最高者为
接下来的365天,怪兽与日历会共同陪伴你
你喜欢哪个颜色哒?记得尽快回复后台地址和联系方式~
这是今年的最后一次推送了
节 日 快 乐 , 明 年 见 !
如果你也想成为 小 怪 兽 的 星 星
点击“阅读原文” 查看投稿方式
相关推荐
友情链接
Copyright © 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香港腕表价格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