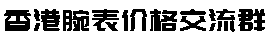
2021-06-22 06:55:19
你与好故事,只差一个关注的距离
每天读点故事APP独家签约作者:塔克风
禁止转载
1
我感觉到透不过气来,很难受,那些家伙像是在挤走我仅有的最后一点空气。
难逃一死了,但我想在死之前把自己经历的一切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有人在我的尸体旁边看到这本晨光笔记本,先不要读下去,立刻想办法处理掉这些书柜里的书,建议用火烧,别怕引起火灾。如果你不及时这么做的话,它们会杀死你,在你还没有读完本句话的时候。
哎,我真怕在你看到这个本子之前,它就被那些恶魔给销毁了,就像它们即将做的,销毁我的生命。
我的名字叫做孙子涵(读到这里你可以对照着我那无光的死面,轻轻地念出这三个字)。现在你所处的这间公寓本是我爷爷的房产,我爷爷在五个月前死了,这栋房子就理所当然地归到了他的独生子,也就是我的爸爸名下。
我的爸爸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我妹妹,孙子怡。
我的妹妹事业家庭美满,不像我,大龄光棍一个,戴着一个假艺术家的帽子,画画赚钱,住所是臭水桥下的廉价平房。
爷爷死了一个月后,爸爸煞有介事地把我叫过来,说我可以住到爷爷生前的公寓里,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当然不介意。
爷爷家的公寓有将近120平米,水电煤齐全,跟我那时的住所相比简直就是伊甸园。我可不怕什么灵魂归来云云的迷信说法,再说就算真的归来了,那又如何?那可是我的亲爷爷呀!
“那些书……”爸爸咬着字喃喃道。
爷爷的公寓里有大约三万本书,从红楼梦到悲惨世界,从鲁迅到斯蒂芬·金,从客厅到卧室,几乎每一间房间都有书柜,还不止一个。我们每次到访独居的爷爷家,总是戏称为“去图书馆了”。
他老人家是一个书虫,爱书如命,应该这么说。爱看书对于一个报社的老编辑来说不算稀奇事儿,但他用毕生的积蓄买书,买了一辈子书,堆满了家的三分之二,这就很奇葩了。
爸爸问如果我住进去了,会如何处置那如山一般的书籍。
“我知道这些书对于爷爷来说意味着什么。”知道?哼,现在想想,当时我知道的还是太少了,“我不会动它们的,毕竟它们在家里,就像爷爷也在似的,一切都没变的感觉,多好?”
爸爸点点头,把那串银色的钥匙扔给了我,说我随时可以住进去,那里的所有家具都没有动过。
一想到可以睡在那舒舒服服的大床上,我的心底一阵暗喜。就这样,噩梦正式开始了,我攥着开启恶魔之门的钥匙,于2017年3月1日正式住进了爷爷的私人图书馆。
2
我的新家处于长寿街长寿九村122号402,你们也可以理解为是老人的故居。
这栋公寓的结构十分常见,可能就和你家的结构相同。三室两厅一卫一厨,外加一个阳台。一个主卧,两个次卧。
爷爷是41岁才当上报社编辑的,在这之前,他是一个周游世界的浪子,靠给多家报社供稿赚钱不菲,然后辗转各地购买原版书。
在上海定居之后,他买了这栋房子,把那几千本跟随他周游世界的书籍全部安顿了下来,然后始终在不断购置。所以造成的局面是——在这里,不管哪个卧室,甚至是厕所,只要你睁着眼睛,你看到的百分之九十都是书柜,和书。
但我并不觉得不适应,甚至感觉十分亲切——从小,这里就是我和我妹的玩乐天堂。
我们在整个公寓错综复杂的书柜间捉迷藏,比赛谁先爬到矮柜的顶端,或者是把谁心爱的贴纸藏在随意一本书里,直到把对方找哭了才公布答案……有一次我把答案给忘了,子怡声称要杀了我。
在那些和这里有关的,无忧无虑的时光里,爷爷像是一个画外的角色,总是坐在角落里看书,成为风景的一部分,只有在我们的百般纠缠下,他才会对两个小孩加以理睬。
“你们为什么不喜欢看书呢?”这是爷爷对我和子怡说过最多的话。
我们不爱看书,但是十分喜欢这个图书馆。偶尔,放寒假暑假,老师要求我们阅读指定名著的时候,我们才会以正确的打开方式光顾这里。
还记得高中的一个寒假,老师叫我们看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要写1000字的读后感。我强耐着性子在爷爷这儿看,而爷爷一副兴奋的样子,每天都问我看到哪个情节了,然后试着和我讨论一些深奥的问题。我没有一次让他满意过。
是的,爷爷对书很痴迷,我可以负责地说,他看过这里的每一本书,甚至能说出任意一本书哪一页是关于什么的。
他对书的热爱确实到了偏激的程度——子怡有一次弄坏沈从文的《边城》,就是不慎撕碎了一个书角,爷爷第一次对孙女大发雷霆,看得我都难受极了。
“你弄疼它了!”他这么说,十分惊悚。
从此,即使这里有我们需要的书,我们也会另买来看。
就这样,高中时期,我们对书屋的感情渐渐地疏远了。
看到这里,可能你会想了,我的爷爷这么喜欢看书,还是从事文字工作的,应该有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吧?
错了,他别说志同道合的朋友了,就连一个酒肉朋友都没有。
他的性格孤僻,奇怪。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也慢慢地体会到了——这个老家伙的世界里只有书,他每天洗完澡还要给书“洗澡”。那一套昂贵的,据说是大不列颠博物馆级别的书籍修复保护维持套装,他要按照书的新旧,一张列表,每天维护20本,要花费4个多小时的时间。
他不再看书了,因为该看的书全部都看完了。
“我看见爷爷在跟它们说话……”子怡那天瞪着浑圆的眼睛告诉我,“跟书说话,在跟一本外国原版书说外语……”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十分怪异的老头。
他活了94岁,在自己书柜前给书“洗澡”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场暴毙。尸体于两天后被去看望的爸爸发现,已经开始发臭了。
听爸爸说,他死的时候正在清理一本叫做《绿里奇迹》的书,斯蒂芬·金写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是一本相对较新的书,跟那些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和爱伦坡比的话。
他就死在这里。
在把行李箱靠在卧室的书桌边时,我心有余悸地想。
好久没有回来这里了。说来愧疚,自从上大学之后,我就一次都没有拜访过爷爷了。
不知道是我不适应了,还是时过境迁,这里竟然多了一丝阴森的味道,偌大的公寓里,独自一人,貌似有几双变形的眼睛在哪处盯着我。确实有,确实有的。
我的行李很少,几件四季通用的衣物,画板和颜料,洗漱用品,还有一颗向着艺术的心。
等我收拾完,天还没黑,我就在爷爷的一米四单人床上躺下了。爷爷睡了大半辈子单人床。我没见过我的奶奶,她身为高龄产妇,在为爷爷生第二胎的时候难产死了。
就当我在黄昏窗边的大床上昏昏欲睡的时候,那些我暂且不知道其真面目的恶魔就已经计划着要给我这个小子一个狠狠的下马威了。
3
我是被渴醒的。
电风扇在上头哗哗作响。我不记得我开过电风扇,可能是睡到一半觉得闷,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打开的吧?
我这么想着,从床上爬起来,双脚触及冰凉刺骨的大理石地板。这里并没有直接可以饮用的水,如果子怡也在的话,她肯定知道要在睡觉前先烧一壶水的。妈的,我想,看来自己真的需要一个女人。
就在我悻悻地回屋,决定忍耐到早上的时候,一个东西毫无预兆地闯入我的眼帘——
那是两本装帧几乎一样的厚书,整齐地摆放在我的,也就是爷爷生前的床头柜上,紧贴着床沿,跟我的枕头只差了一拳的距离。
我很是纳闷,仔细地回想今天早些时候,床头柜上有没有东西……在我的印象里,床头柜上除了自己摘下的近视眼镜,就什么也没有了。
我打开灯,眯着眼睛,拿起放在上面的一本,贴近脸费劲地看了一会,等强光对双眼的侵蚀慢慢褪去,我才看清那一个加粗的黑体字:飘。
上集,美,玛格丽特·米切尔著。
不知道为什么,我握着书封的手开始微微发抖,就像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在练习平举双臂时的反应一样——如果这是上集,那下面这个装帧一样的必定是下集了……我确认完之后,更加觉得费解,因为记忆已经越来越清晰了,在上床前,床头柜上并没有这两本书。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人进来了,在我睡着之后。第二反应是闹鬼了。
很快,这两个站不住脚的猜测就全部被否定掉了。门窗都锁得好好的,再说,我是神经脆弱体质,如果有人闯入,我一定会醒过来的。小时候,只要有家人比我先醒,不管他们怎么保持安静,都会吵醒熟睡的我。
这么安慰着自己,却发现自己越来越慌张了。
我猛地摇摇头,决定不去管它了,闹鬼就闹鬼吧,如果这里有鬼,也只会是爷爷。我不怕爷爷。
再说了,记忆这种东西是会出错的,谁能打包票说自己从来就没有记错过一件事情。可能这两本书就是我临睡前拿的,想重温一下高中的寒假时光?只是那时和现在都太困了,所以记不清楚了。
就这样,一阵困意袭来,我关上灯,又一头睡了过去。后半夜,我做了一个梦。
4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一趟广告公司,去交他们叫我创作的一些底图。
“喂,孙子涵!”
负责人突然从背后叫住我。我诧异地回头,看见他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你不要报酬了?”
我承认我昨天没有睡好,一早起来,浑身酸痛,感觉自己像是一根被猛地捏变形的绿茄子。
后半夜梦的画面还在脑中萦绕,我试着仔细去捕捉,它却快速地消逝了,无影无踪。
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梦,不能肯定是噩梦,但我一定是在梦里做了什么耗神的事情,使得脑袋爆晕,身子摊在床上发软酸疼动弹不得。
在广告公司出了一点小糗之后,我有些郁闷,有些乏累地回到了“图书馆”。这里迎接我归来的不再是蟑螂、老鼠、四脚蛇,而是书、书柜。我疲惫地对它们笑笑,就像以前对那些小强做的一样。
穿过白琥珀色大理石上面一个个摆放规则复杂的书柜,我闪进了卧室,一屁股躺在床上——卧室的布局你肯定能看到,因为我就是死在这里的。
20平米的大小,西南角的窗户,东北角的床,另外两个角落分别有一个硕大的七层红木书柜。里面装满了书,密密麻麻。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我保证你坚持不了三秒。
对!书桌,还有就是这个书桌,我正坐在它旁边,书写着我遭遇的一切,我的临终遗言,我生命中最后的几个月……
起床的时候,我没有把那两本奇怪出现的书从床头柜上拿走,而是急匆匆地换好衣服出门交图去了——但当我回来的时候,它们就像人间蒸发一样,从床边消失不见了,柜子上面空无一物。
咦?我的心咯噔一下,霎时冷汗直冒。
突然,一股强烈的冲动,抛开理智和常识,涌上了心头——我疯了似的打开卧室床边的那两台大书柜,眼睛仔细地扫视起来。肯定有人来过!我告诉自己,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那个人在耍我!在装神弄鬼。会是谁呢?
就在我的心中浮现出一个最佳人选的时候,两个柜子里的书已被清点完毕,那两本上个世纪出版的《飘》并不在卧室的书柜里。
难道在其他房间吗?又抑或它们已经不在这栋房子里了。
我想象闯入者拿着这两本专门用来吓唬我的书,在我熟睡的时候轻轻放在床头,又在今早我离开后潜入并拿走了它们,想要再吓唬我一次……
我才不会如此轻易地被吓到。没错,就在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自以为明白,应该说。一股怒气蹭地蹿上脑袋,我打算直接去找他,那个表里不一的死家伙!
5
子怡的老公,也就是我的妹夫张爽,他在爸爸做出这个决定后,不止一次地对我住进这件房子有意见,说是得事先征得子怡的同意才行……妈的,我妹都没说话,轮到你来插脚?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他在吓唬我。
到了他们家之后,我一眼看见张爽那小子拿着两本书。怒气越来越旺,我快步走过去,勒住他的脖子,他干嚎一声,像个女人一样——真的不知道子怡是看上他哪一点了?那两本书“咚”地砸到了地板上。
“哥!你疯了!”
我也觉得自己是有一点疯了。张爽的眼神就像是案板上的鲫鱼,我让自己平静,把手放了下来。
“找死啊!”他一边摸着脖子一边喊。如果他稍微有那么一点种,应该在刚才就喊出来。
“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你在哪里?”
“什么?”
“我问你!昨天晚上半夜和今天上午,你是不是到过我家?!”
“你到底在说什么?”他语无伦次起来,很讨厌的样子。最后,还是子怡回答的我,告诉我,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她老公都跟自己在一起,并且问我出什么事情了。
我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弯腰去捡那落地的两本书——事实胜于雄辩,不是吗?可当我把它们拿起来的时候,看着那摩登的封皮,和艺术字的标题,我霎时说不出话来了。
《在股市里摸爬求胜——我炒股的这十年》?
“你真的昨晚到现在,一直在家?”
张爽点点头,看着我的势气弱了下去,便开始无耻地反击,还说什么看在我是子怡哥哥的份上,就不跟我一般见识了……我突然觉得头很晕,踉跄地出了门。孙子怡追了上来。
“哥,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没什么事情!”我甩掉了她,上了一辆刚好开过来的702路公交车,回到了家。
家里,我再次看见了那两本阴魂不散的《飘》,不过不是在卧室的床头柜上了,而是在进门的鞋架上,就这么竖立着,没有任何支撑的东西,像是被故意摆成这个样子的。一前一后,上卷封面上的塔拉庄园好像长了眼睛,就这么看着刚刚回来的我。
我终于忍不住,放声尖叫起来。
6
我把那两本天煞的《飘》给烧了。
那天,看见它们立在鞋架上,用一种诡异的方式欢迎我。我先是尖叫,然后便恢复理智,想不能一直这么下去了。于是就找来打火机(我不抽烟,随身带打火机的习惯源自老租房那个总是点不起来的灶台),把其点燃,扔进了垃圾桶,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烧成灰,然后把灰烬倒下窗户。
然后一段时间,一度再也没有怪事了。有,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吧?这期间没有太多要记录的,只有一件事情——约翰·科菲。
我一直做噩梦,很可怕的噩梦,在爷爷生前的床上,每次就像那天描述的一样,睁开眼睛,不到几秒,关于梦境的记忆就全盘消失了。
但是我冥冥中感觉到,这些梦都是相同的。
是不是睡在死人的床上都会做可怕的、难以言状的梦?不是的。
最后,有一天,我发现了真相,一个让事情更加匪夷所思的真相。
我或许真的需要一个女人,因为如果我能时常整理床铺的话,或许就能更早发现它了——斯蒂芬·金的《绿里奇迹》,就这么摊开着,压在我的枕头底下。
我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是我知道,这是爷爷临死前最后清理的一本书,他是枕在这本书上死去的……我慢慢地,像触碰诅咒似的摸了摸它,顿时一身的鸡皮疙瘩。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感觉它也同时在摸我。
具体摊在哪一页我忘记了,不过我记得那页上面的内容,大致地看了一下——写的是给一个纵火的死刑犯执行电刑,第一人称的主人公监督,结果头套的海绵是干的,死刑犯死相凄惨,惨不忍睹……
我被那鼻涕脑浆的描写怔住了。简直,简直太重口了……突然,我的脑海深处想起了什么!
这一页的内容,出现在我的梦里。所有的梦里,应该说!
在梦里,我是这个死刑犯,他们在用椅子电我,还没有弄湿海绵!让我脑浆四溅,鼻涕体液横流。那种痛苦很真实,只是梦醒就忘了,现在,我全部记了起来,腿一软,跪到了床前,就像一个准备的青少年的模样。
这可比那个感觉狼狈得多。
这本书是谁放的?我在脑袋里问自己。是爸爸吗?发现爷爷死在这上面之后吗,把书放在了枕头底下?然后让我住进来……不可能吧?
它是自己进来的。一个若有似无的声音告诉我,我跳了起来。
最后,抛开一切可怕的东西不想,我把这本《绿里奇迹》抽了出来,合上。在放回书架之前,又不安地翻了一翻。
这本书主要写了一个叫做约翰·科菲的男人,他是一个大个子黑人,因为两个女孩的罪名而被判死刑。在服刑期间,“我”发现了他的魔力,和他的清白,是一个恐怖中带着感人的故事。
约翰·科菲……我咽了咽口水。在梦里,那个站在我电椅前,看我死去的人,形象并不像那个狱警,更像是……约翰·科菲!
那天,我已经感觉到了恐怖的信号,并把此书也烧掉了。
我觉得这间屋子里可能是有魔鬼……书魔……不管它是什么,只是那时的我还没法相信接受,仍在心里排斥这个非唯物理论。直到一个月后,就是我烧毁《飘》后的整整两个月零四天……
7
它们都回来了。
四月的最后一天,我正在卧室里面画画,只听门外响起一阵轻微的敲门声。
“谁?”
……
“谁?”
最后,我百般不情愿地走出房间,透过猫眼向外看去……一个人也没有。
估计又是楼上那个小孩的恶作剧,我想。刚转头,敲门声又响了,这回动静大了一些。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撞开了门,想要给那个恶作剧的家伙一个措手不及。
走廊上空荡荡的,还是没有半个人影。
“呃!”跑得还挺快。
我有些晦气地关好门,准备回卧室继续画我的旷世大作——这不是工作,而是我自己想要画的。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筹钱办一个个人的艺术绘画展,然后此生无憾。那是一只五彩的凤凰,用的是西方的油墨画法,敲门声响起的时候我正在给它画上翅膀,一双绮丽无比的翅膀。
就在卧室的门槛边,我又看到了我的两个老朋友。
一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脑回路跟不上了——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它们,随后开始头上冒汗,心脏慢慢地提起来,直到半分钟后上了嗓子眼……
紧接着我短发冲冠似的立起,眼睛开始酸涩,因为盯得久了——《飘》小姐和《绿里奇迹》先生正有些不规整地躺在大理石地板上,仿佛在没人发现的情况下,它们就会长驱直入地到卧室里面去。
天呐!最后,我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那三本被我烧成灰烬的书回来了,它们敲了门,然后进屋,就这么回来了……
我难以置信地捧起那三本书,都是硬质封皮,标准32开的印刷纸,在手里任我翻来覆去,丝毫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但是它们回来了。那个若有似无的声音再次跟我说道。
我浑身一个机灵,两只手剧烈颤抖起来——《飘》的下卷封皮上有一道划痕,是我在烧毁它们的那天无意划上去的……
这三本书是魔鬼!我对自己说。
然后开窗,我直接把它们扔进了后面的护城河里。看着它们顺着水流向下游飘去,我真的是安心了不少。但脑袋里的另一个声音告诉我,它们会回来的,你烧都没有烧死它们,它们肯定会回来的,而且会比上次更快!
是的,比上次更快。
8
我得趁它们回来之前,搬离这里。
这是我唯一想到能解救自己于书魔的办法——没错,我叫它们书魔,这估计是最贴切的叫法了。
它们是有灵魂的,它们正在蠢蠢欲动,,然后再不断地恐吓我……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是真的,我怕它们会杀了我。
我想起了爷爷,他那深潭一般浑浊的眼神,在独自一人的深夜,对着这些书本呓语……
他给了它们灵魂。
在出门之前,我再次环视那十几排书架——各种书,老书新书,古文书原版书,理论书通俗读物……它们都是有灵魂的吗?就跟那两本《飘》与《绿里奇迹》一样?
带着这个让人后怕的疑问,我一秒也不迟疑地带着行李离开了。
回到之前那座大桥下的租房,房东已经把我的房间租给别人了。
透过窗户,我看见一个国产雷鬼,披头散发,正在用一把叫做吉他的棍子发出噪音。看来这个破烂地方也是挺抢手的?我心情凝重地朝窗里面竖了竖中指。
我本来应该继续寻找出租房、不再回到那栋房子的。现在想想,那一天的种种,真的是老天爷指定了要置我于死地呀……
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在我走出第三家租房中介,唏嘘着还是没有合适的房子时,接到了一通电话——是一个陌生号码,那头的人来头不小,说看中我的画作,想要面谈并长期合作。
我的血脉在那一瞬间,顿时就沸腾了。带着画笔游走江湖将近五年,有在公园里给人画过素描,有给各大广告公司画插图,有给一些出名的画家打下手……那位给出的机会与待遇简直就是梦寐以求。我马上就答应下来。
“那就去你家里谈吧,地址?”
我顺口就报了一个地址,是我桥下出租屋的地址。然后一时语塞,连忙收回——那里已经住了一个雷鬼了。况且在那种破烂地方谈那么重要的事情……我不可避免地想到了爷爷的图书馆,钥匙还在我的包里。
“长寿九村122号402。”我如是说,对方爽快地答应了,并叫我可以准备一下了,他很快就来。
当时是晚饭饭点,于是,我想也没想地,火速去超市买了一些熟食和啤酒,火速赶回了图书馆。进门五分钟后,坐在那熟悉的,本以为再也不见的一群书柜中间,恐惧再次迎面而来。
又回来了……
书柜,书,书柜,书……祸从口出,我开始后悔自己的鲁莽。明明可以报爸妈家地址的。
在那人还没到的时间里,我仔细地翻找了整个房子,没有看见那三本书魔的身影。
我们聊得很欢快,他很喜欢我的画作,在茫茫人海里,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人真的是太幸运了。殊不知,这种幸运只会维持几个小时的时间,很快我就会发现自己被逼入了致命的困境。
“那么,就这么说定了!”
“好的!”见他要走,我便起身准备送行,谁知因为喝了太多的酒(我的酒量一直就很不好),一个趔趄,又趴了下来。最后,还是让人家帮我扶到床上的。想来真的是很糗啊。
就在我入睡的那一刻,天地昏暗。相信我,那个时候,书魔们的舞会就已经开始了。
9
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分辨,那晚发生的一切是梦境,还是真实?
可以肯定的是,在舞会开始之前,我正在做梦——具体是什么梦呢?我只记得最后的情节——自己在一架楼梯上攀登,楼梯直插云霄,没有止境。我越爬越累,越爬越累,最后竟一脚踩空——
“啊!”我闷声叫着,从床上坐起来,那种恐怖的坠落感还在脑海中挥散不去,心脏一阵骤停,紧接着怦怦狂跳起来——有几本封皮泛黄的书隔着被子,压在我的腿上。因为还没有睡醒,那一刻,我并不觉得几本普通的书自己跑到床上有什么不对。
不对!肯定不对!
我开始尖叫,一掀被子,把那几本老书抖了下去,然后用被子盖住头,蜷缩起来,瑟瑟发抖。
是书魔,书魔又回来了!
在被子里躲了半晌,我越发觉得奇怪——为什么把那几本书抖下去的时候,没有听见它们落地的响声?想到这里,我的脑袋像是有手榴弹炸开一般,是酒精的作用,从小到大,我的酒量就不是很好。
为了在“安全”的氛围下一探究竟,我像小孩子那样,在被子里慢慢地调整身子,面朝书柜的方向,也就是刚刚那几本书被扔下去的方向,腾出手,掀开一条很细的缝,向外边看去——
那时的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应对一切的准备,很显然,准备不足——就像是中土之战的霍比特人大军,在幽暗的卧室地板上已布满了书籍。它们横竖整齐地堆砌着,一排排,一列列,有几摞特别高,都超过了床沿,像一株株打激素的邪恶植物,在地板上野蛮生长。
我使劲揉揉眼睛,这幅景象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不见,反而更加真实了。那些书占据了房间里每一处可以插脚的地方,虽然它们本身没有眼睛,但我仍有一种被一堆眼睛盯着看的感觉:
“孙子涵,快点下来吧,舞会开始了!”一个虚无缥缈,分不出性别的声音在我的脑中回响,很不真实,却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得不能再真实了。
舞会?什么舞会?我想。
“书魔的舞会。”那个声音再次响起,回答道。我浑身一颤,赶紧把被子盖住,眼前瞬间陷入一片让人略微安心的黑暗中。
“别害羞嘛,孙子涵,出来跳舞了!”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音乐,它像是那些低语一样,找不到音源,无法辨别是从哪个方向发出来的,但确实很清晰。滴滴答,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答……
管风琴。
弦乐队。
长号小号也来了。
伴随着音乐一块响起的,是震耳欲聋的磕绊声。我不知道是着了什么魔,竟慢慢地把身子从被窝里滑出来——
只见那些书,各种各样的书,简装的,精装的,32K的,A5的,通俗的,严肃的,都整齐划一地排成一个个圈,跳起了踢踏舞。它们长方的身体左右跳跃,两个朝下的书脚交叠触地,这便是磕绊声的来源。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的是疯了。
“你没疯,孙子涵,你只是需要跳舞。”
就像是花式舞蹈队的职业选手,这些书开始排队形,队形千变万化。
音乐进入第二乐章,(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客厅里的,餐厅里的,甚至厕所里的书柜也自行打开,在黑暗中,那里头的书就像是蝗虫一样从各层书架上涌下来,然后朝向卧室这里行进。
“来吧,一起跳舞吧,孙子涵!”
我没有答应,一直缩到靠墙的墙角。随着卧室里书的数量越来越多,有些书直接蹦到了床上,我的脚边,继续跳舞,时不时地摩挲到我的脚踝,是那种纸张特有的冰冷温度。
这是梦。我沉着下来,告诉自己。这他妈的肯定是梦,清醒梦。只要再忍一会,醒来保证还是好好的。
但在内心深处,我并不相信这句话。
所有的书蜂拥而至,挤在这个狭窄不过二十平米的空间里。我开始透不过气来,不知道是过度的惊吓导致的,还是说,氧气全被这些跳舞的书给吸走了?
它们是书魔,它们也会呼吸,像人一样。
我终于尖叫起来,叫得很响,结果绊到了一本红皮的厚书,直接摔下床,跌入那恐怖迷离的书海里。
很多的书被我压倒,然后就像死了一样,不再动了。旁边的书开始往我的身上扑,就像是撒娇的小猫一样,蹭在我滚烫的脸颊上。
这可一点也不可爱。
我试着从一大堆会行走的书籍中爬出来,但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可能你并不理解,如果也亲身体验一番,你也一定会理解的——刚刚找到支撑点,膝盖就被哪本书狠狠地撞到(我相信它们都不是故意的);眼看就要挤到门口了,稍稍一松懈,就被一股强大的推力推回原地。
我哭了,哭得很惨,但没有人理我,也没有书理我,大家只是在继续舞蹈。
音乐戛然而止,代表着第二乐章的结束(他妈的这到底是哪一首曲子,是一首真实存在的曲子吗?)所有书都停住了,像是被抽掉了本不该有的魂魄一般,纷纷瘫倒在地上。
我踉跄地冲出卧室。
接下来的事情发展顺序我有些记不清了。原谅我,现在屋里的氧气已经所剩无几,我提笔的手也开始发软。
总之,它们再次回来了!像是凯旋的红十字军,整齐地立在茶几上,封皮上还滴着护城河清绿色的水。《绿里奇迹》魔王,和《飘》双胞胎女王。我隐隐听到一阵邪魅的笑容,笑声从心底发出来。
“你无法杀死书魔,孙子涵,魔王们更是百毒不侵!”
第三乐章,激昂的弦乐主奏响起……嗯,好像是那时候响起的——响起的同时,那本《绿里奇迹》先行从茶几上跳下来,我听见后边的卧室里,窸窸窣窣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响。就像一股龙卷风,由书魔组成的龙卷风,呼啸着飞腾出来,把我整个人包住,强行地拽了回去。
它们都长着眼睛。
10
次日早晨,我从床上醒来,只觉得浑身酸痛,像是做了一个疯狂的梦。
怎么这么黑?天还没亮吗?
我的头开始疼起来。我这是在哪里?在爷爷的图书馆吗?妈的我怎么又回来了?好像是为了一个客人……什么客人啊……欣赏我画作,想要跟我长期合作的客人,没错……后来怎么了?后来……喝多了?在这里过了夜吗?
好像是的。
一想到又在这天煞闹鬼的地方过了夜,我浑身一个哆嗦,摸着黑下了床,想要出门,却被一道墙面狠狠地撞了一下,摔回了床上。
嗯?
是不是哪里不对?
确实,黑得太不像话了,明明开着窗,却连月光都没有——等等,窗呢?
眼睛慢慢恢复视力,我手忙脚乱地在黑暗中寻找手机,想看时间,却死活找不到。最后抓到了床头柜上的夜光电子表,表盘上显示的数字是上午九点。
我惊骇地抬头,环顾四周。
不会吧……
是墙,由各种书堆砌成的墙,把我团团地围住,连一点缝隙都没有。我感觉渐渐地透不过气来。
书魔吗……我咽了咽口水,记起了昨晚那个疯狂的梦,历历在目,真实得不像是梦。
舞会,书魔,还有那句“一起跳舞吧,孙子涵。”
现在想想,那场舞会肯定是为我举办,是我的临终送行。
它们打算用法术抽干空气,然后闷死我,没错。
直到现在,我都没能逃出去,应该有整整一天的时间了吧?那些书像是事先排演好的一样,塞得十分十分紧,使用全身的力气都撞不开。就好比是一个完美的拼图,每一块都是紧紧的,无缝衔接。
而且,它们好像处理了我的手机,我找不到它了,无法呼救。
我决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从头到尾地。
所以,请说服自己相信,这里的每一个字绝对,绝对属实。
如果你读到这里,还是没有对那些书魔采取行动的话,那是你命大——用火烧,并不是为了彻底烧死它们。它们百毒不侵,但这起码可以给你逃跑的时间,或许你下次可以让一支军队过来,彻底消灭它们?
下面是我对书魔的一些推测:爷爷赋予了它们生命,在暗夜里和它们说话,就像子怡看见的那样。他害怕弄疼它们,因为它们是有生命的,爷爷很清楚这一点。
它们也跳舞吗?在跟爷爷生活的时候?爷爷对这些书很好,不容置疑,所以爷爷去世之后,它们疯了吗?开始袭击我,这个愣头愣脑,随爷爷之后住进这间图书馆的人?
可我是他的孙子,它们没有理由攻击我。
想到这里,我开始怀疑另一件事情——爷爷的死,难道也是这些家伙造成的?
这个想法让我不寒而栗。别在意这一行的划痕,我的笔抖掉了。
在医生,和所有知情人士的角度,爷爷的死因是突发脑溢血。但如果,不是突发,是有人蓄谋的呢?
不是人,是书。
就像它们现在对我做的一样,把爷爷团团围住,然后爷爷在窒息的恐惧中突发恶疾?
那个老骨头,在去世的前几天,还十分健康,脑血管也比大部分的同龄老人强得多。
也许,给没有生命的东西以生命,比夺走任何生命都要荒谬得多。
哎,真是天大的玩笑啊,哈,哈。
尾声
新闻报道:
今天,在长寿新村发生了一件怪事。
根据知情人爆料,一名年轻的自由画家死在了爷爷的故居里。其爷爷生前曾是多个知名杂志的主编,爱好藏书。
在年轻人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屋内十分干净,没有任何异常痕迹——只有例常的家具,和几个书柜,放满了各种书籍。死者系缺氧窒息而死,但脖子并没有任何被勒的痕迹,警方至今没有查出具体的死因。
这也引起各界人士的纷纷猜测,但都没有准确的答案。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尸体的右手紧紧攥着一支笔,手指有些许压迫性红肿,像是在持续地书写什么东西,但现场并没有找到任何纸张、笔记本之类的东西。警方怀疑死者给后人留下了文字线索。
但搜遍整个屋子,甚至翻开每一个书柜筛查,都没有找到任何笔迹。
最新的官方猜测,死者的死因可能系某种奇特的自身生理原因?众所周知,没有一个人会在一间有窗的卧室里被活活憋死……(原标题:书魔)
长按二维码下载【每天读点故事】
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每天读点故事app」——你的随身精品故事库
如长按二维码无效,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相关推荐
友情链接
Copyright © 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香港腕表价格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