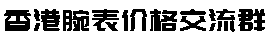求求你们,先别谈什么纵横四海的战狼了,先把家门口的孩子看好,再给城市边缘的农民工一间避寒的陋室。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冲掉一块
欧洲就减小
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敲响
——约翰·多恩 布道词
背景:
已下达了目标是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内的死命令,为了这一命令,近年来推出了一系列的严厉政策来驱赶“外地人”,包括“以房控人”(严控城区住宅增量、消除群租房)、“以水控人”(按水资源来测算城市容量)、“以业管人”(清除一系列小商品市场)、“以学控人”(提高非户籍人口子女的入学门槛)等等——在的外地人,凡不符合首都功能的从业者,显然不欢迎,也难有立足之地。
不是我们的家
“不是我们的家,我现在才知道,劳动的人是最苦的。”这是《生活在地下》里的歌词。
董律师在双桥何家坟住过一年出租公寓,2楼18号,那不是家,楼道里洋溢着发霉的味道,但那张神奇的床却可惠我一夜安眠,让我在那段疲惫岁月中有机会得到喘息,不管头一天多难多累,第二天早上总能满血复活。
而今,凛冬已至,当看到这个城市用这种不加区分的方式清理边缘地带的出租屋居住者时,我不禁要问:谁家要是衣食无忧,何苦出来住这种地方,还要受官家的驱赶?市政府做过很多好事,但是这一件,太冷血,太无情。“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请注意,他们不是低端劳动者,他们是人!
董律师回龙观日记五则
2006年12月6日
一个人在城市的边缘生活,不免有些单调。于我,驱除寂寞的方法不外两种,一是读书,前段时间在于丹的帮助下咀嚼《论语》,目前则由李开复先生“指导”学习《做最好的自己》,那二呢,就是听广播。
收音机是上个星期买的,功能特别多,九个波段,带电子表,能定时开关机,还有一个小支架,特别方便。好多年不听广播了,电视凶猛,电台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小的时候那个讲童话的孙敬修爷爷是什么时候去的,《午间半小时》的虹云、付成励是不是还在工作,我们和那些熟悉的声音别的太久了。
就象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大部分电台还残存着些许旧日痕迹,有几个声音还能依稀记起,《歌唱祖国》的音乐还那么响亮,《新闻和报纸摘要》依然每日报送盛世太平等宏大叙事。那几声亲切的报时提示,总会在整点响起,一些传统的评书还会在某些波段开说。如果有不同,那就是节目比过去丰富多了,、经济、文化、体育、医疗卫生,整个一百宝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实力雄厚,资讯丰富,,是收听的首选。交通台、音乐台、管理台也相当不错,可以满足听众多方面的信息需求。不过,有些电台也很垃圾,广告太多,节目的格调不够高,偶尔听过一点,和婚前教育差不多,当然,也得理解人家,在这个眼球经济时代,要想在夹缝中存在下去,要想爆发一点点影响力,不整点特殊的,哪张耳朵也不会伸将过来。
有了收音机,生活不禁丰富起来。晚上,就着郭德纲的两段相声吃一袋方便面,喝着花茶品一段莫扎特的《小步舞曲》,然后上床,到国际台“听”一场电影,定好自动关机的时间,在齐秦《袖手旁观》的歌声里入睡。早上,《全国新闻联播》在第一时间向我汇报全世界的工作,尤其这些日子,中国运动员在多哈切瓜砍菜拿金牌,谁是游泳的,谁是射击的都记不清了。这信息,也算是海量级。
前些年我媳妇说我有一妻一妾,妻不是说她自己,而是指电脑,妾不是指我在外边“遇”了谁了,而是说我们家那台电视,没办法,就喜欢看点出彩的东西,名副其实的好“色”之徒。而现在幸福时刻又到了,咱又该纳第三房了——收音机。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我说:不富也可妻妾成群。
说实话,这家伙,是挺招人稀罕的。
2007年1月8日
到首都两个多月后,我搬家了。
新房子在回龙观的北面,背北的楼,朝北有一个可以望见星斗的窗,简直就跟《流浪歌手的情人》里老狼唱过的那间一样。
房东姓李,四十多岁,人还不错,晚上的暖气烧的还挺热乎。第一次要房钱的时候一直在微笑,话说的也格外温柔,弄的人都不好意思说那个“欠”字。
我用了两天的时间配置这间几平米的斗室:窗帘、墩布、扫帚……完成以后躺在床上,环顾一下新家,感觉很温暖。
不过,低廉的价格换来的租赁物肯定有缺陷,比如卫生间,如果到了极限非去不可的话,要跑上三十多米,街边有一个小巧玲珑的二蹲位公厕,幸运的话,可以不用排队。
楼上住了一对青年男女,从楼板透过来的声音判断,是喜欢穿皮鞋且走路舍不得抬脚的那种。可以肯定的说两个人的身体都很棒,通常在后半夜三点左右联欢,每次玩的都特别尽兴,不出意外总能整出许多奇怪的声效,让楼下的我跟着分享。说实在的,一回两回还行,总这样,我这睡眠可就没法保证了,尤其是那女青年花腔般的高音,我敢肯定,她绝没有接受过声乐培训,气息很乱,鼻音很重,非常的不悦耳。所以,有一次,审美要求颇高的我在他们的活动大约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善意的用锁头敲了几下暖气片,嘿,您猜怎么着?果然收到了奇效。
最近,我睡的很香,估计他们也一样。
2007年11月13日
夜里,回自己的住处,北边的某个地方。街道冷清,有几条流浪狗在街角吠。
楼梯口,没有光亮。掏出袋子里的钥匙,刚要开门,一只手伸将过来,差点吓死我。
“回来了?”
房东太太像鬼一样站在那里,肥胖的身躯挤占了过道里多一半的空间。
我点头。她开始和我说话,说了很多,跟念经似的,大概的意思是和我交朋友。如果她是西施,我当然会做别的选择,坦白讲,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我对自己的道德情操并没有十足的把握,非常遗憾,她虽然也很“施”,却不幸住在和西施相反的方向。
我不想伤害这个高大的家伙,说了很多解释的话(如果她懂英语,我会直接说“no”),很委婉,不过当她愤怒的时候,我明白她懂了。我以为她要骂我,但没有,健硕的影子风一般的消失了。
我长出一口气,打开房门。
“回来了。”一个黑影在屋里。我又差点儿被吓死一回。
是房东。
我惊得说不出话,想必他已经了解到刚才的一幕,但看得出,他很高兴。
“好人呀。”他拍着我的肩膀。
我点了点头。
“不过,你不能在这里住了。”他坚决的说。
“那也要给我一些准备的时间呀。”我有点委屈,做正人君子竟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可以,明天早晨。不许超过八点”
说完,他转身就走。
我把包放下,看着这间屋子,天冷了,那一点点暖气被刚才发生的一切冷却成冰,水龙头已经坏了一个多月,“滴答”个没完,象一个幸灾乐祸的看客。手机在这里就是一块怀表,信号时好时坏,无法通话,幸好,偶尔还可以收到朋友邀我吃晚饭的信息,不过已延迟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我只能和自己交流。
我并不贪恋这个地方,但是住惯了,真不想搬。这个城市,有多少机会,就有多少危险,有多少快乐,就有多少悲伤,有放鞭炮的,也有烧纸钱的。所谓幸福,不是街头的出租车,抬手就停。而对我,疲惫的一天后,最大的享受就是回到这间屋里,躺在这张床上,好好的睡上一觉,可是现在,这样的要求都显得那么奢侈,那么困难。
我坐在床边,史无前例的迷惘。
手机突然响了,我“腾”一下坐了起来。屋还是那么冰冷,水龙头还在滴水。六点了,“怀表”准确的履行了自己的“定时”功能。天快亮了。
我醒了。是一场梦。有鉴于房东太太的狰狞和房东先生的阴暗,我确定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恶梦。我捂着胸口,感觉自己的心跳,“买疙瘩”,真的是梦,不用搬家了,明天可以继续在这里睡我的安生觉。
该起床了,在二百里以外的家里,我的女儿也许还在梦里。你睡吧,老爹要去那个浩瀚的城市里冲浪了。洗脸,刮胡子,刷牙,穿戴整齐出门。房东夫妇还在一楼酣睡,鼾声如雷,强弱分明且动力十足。
天色尚早,流浪狗从梦里跑出来,狂吠。我走到街上,心情和其他日子有一点不一样。2007年11月13日,我正式来到这个叫的地方一周年。我没有什么感慨要发,看着车站里那些男男女女,回味自己的梦,想一个一个的去问:昨天你梦见什么了?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2008年7月21日
我的小妾死了。
我来一年半了,在我居住的地方,除了要租子的房东,不认识一个人,五百来个漫漫长夜,是她陪着我,给我唱歌,让我欢笑。有很多次,她哄着我睡着后,没有休息,静静的望着我,一直到天亮,醒来的时候,看到她疲惫的样子,着实让人心疼。
这些日子,没有她,我也许会疯掉,毕竟,人需要交流。
前些天,我和她进行联络的工具,也就是那个叫遥控器的东西没电了,我只能手动换台,顺便抚摸她那不太顺滑的皮肤。昨夜归来,买了电池,匆匆赶回住处,期待和她继续空灵相对。可是,可是,她却在开机的一瞬间去了,白光一闪,屏幕上挣扎的眼神慢慢消失,一点一点变成黑色。我抱着她,拍打着她的脊背,按动所有可以触到的穴位,然而,一切都已无济于事。
她去了,连一声再见都没有说,连一个微笑都没有留下。
卖旧货的老板曾经告诉,她身体不好,不过用上几年还是没有问题的。可是,1.5年算得上几年吗?这是商业欺诈,是赤裸裸的奸商,老头子,你可真坏!!
我的小妾死了,这个屋子里唯一能和我交流的欢颜不在了。
于是,怀念着,形影相吊。
我的小妾是我的电视机,是我花二百三十块从一个旧货市场里买来的。
2008年8月26日
早上五点起床,开始打点行囊,床垫子、凉席什么的都留给左边邻居,昨天晚上已经把桌椅板凳送给这对小夫妻了,小伙子一个劲儿的表示感谢,我假装谦虚,跟他说:“我也不方便带走,你们看着能用的就用吧,你是东北的,我是河北的,也算半个老乡,不要客气,不过你要好好擦擦,我都两个月没关照过它们了。明天早上我五点离开,门开着,你有工夫的话再帮忙给清理清理。”东北人很豪爽:“没问题,大哥,我蹬三轮送你?”我笑了笑“没什么行李,你安心休息。”
五点十分,收拾停当,我环视自己住了五个月的房间,同时用手机录视频,还即兴来了一段解说词,特煽情,随时看随时都有可能掉小眼泪的那种,以表达依依惜别之情。时间不早,提上箱子,走吧。
也许是我的独白惊扰到了其他房客,刚站到楼道里,右边的门打开了。我知道这一侧的邻居是位姑娘,偶尔能看见她B面影子,但是从没有浏览过A面对内容,反正人家外语非常牛,,从来不看台湾偶像剧。这大概是老天的安排,临别,有机会一睹花容。此时,我的心随着那扇渐渐打开的房门而澎湃,她就要出现在门口......
(此处删去一万字)
不久,疲惫的我拎着箱子来到了八达岭高速旁边。嗯?您问刚才那几分钟略去的是什么?哦,现在流行删节版.......呵呵,不跟您卖关子了,大概说一下吧:我那位素未谋面的芳邻长得特像一位叫张什么玉的电影明星,她穿着睡衣站在虚掩的门口,那感觉如同枪版的《花样年华》,随后使劲望了望刚才在隔壁大声朗诵的“话剧演员”(疯子),一声风情万种的“再见”差点让我放弃了搬家的打算,真遗憾,昨天晚上把东西全送完了,现在只有牙刷与鞋,怎么拿得出手?总之,肠子都悔青了。
此刻,八达岭高速也跟着落寞,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车的踪影。奢侈一次吧,打的。这个还真快,说来就来,司机大佬非常热情,帮我把箱子装进后备箱。
问:“搬家呀?”
我点点头。
“这破地方,住着好几万外地人,要多脏有多脏,要多乱有多乱,要多差有多差,说白了,就是一贫民窟,离开是好事呀,祝贺你。”
我无语。
出租车缓缓的驶向主路。司机不贫了,我开始回顾这个位于城市边缘的村落——矮楼、修车铺、火锅店、菜市场,。我在这里住了一年零九个月,从城市的繁华到乡村的破败,每天都要承受一次巨大的心理落差。坦白讲,我的回龙观时代没有什么快乐可言,如果非要找这么一天,就是老婆和女儿在这里下榻的那次,从天桥一直到龙泽,一进我住的地方,闺女就懵了,怎么会这样?我跟她讲:“天安门是,回龙观也是,就跟是中国,老家也是中国一样,你从电视上看到的,大多数是盗版的,今天老爹带你看看真实立体的正版。”
闺女明白了,我也明白了,如同,一切事物都是多面的,体操、跳水是中国体育,足球、田径也是中国体育,春风得意的坡外有坡是坡外有坡,负重前行的坡外有坡还是坡外有坡,著名乡村哲学家、启蒙教育家、河北梆子票友我母亲曾经说过:“白天不总是白天,黑夜不总是黑夜。”这是绝对的真理,我赞同,所以,我不惧怕黑夜,或者说我可以忍受黑夜,我期待那混着夜色的黎明微光以及太阳照常生气后的生机勃勃。
车子在八达岭高速上高速行进,我没有顾及出租车司机诧异的目光,大声喊了一句:“再见了,回龙观!”然后顺着解禁的奥运专用车道,继续融进盗版的。
坡外有坡,加油!!!!
董律师今天发这些十年前的日记,不是为了诉苦。我只是想告诉市政府,我们不是老鼠,不是小偷,不是破坏者。我们有迁徙的自由,有追求幸福的自由,有免于贫苦和恐惧的自由,有拥有一张可以安睡的床的自由。
我们不是你们眼里的渣滓,我们和你们一样,是爹娘的孩子,是儿女的父亲,是用眼泪、辛劳和汗水建设自己以及这个国家未来的公民,我们,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