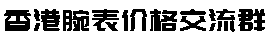![]()
这篇所谓的周年感想其实去年就已动笔却被拖延至今,两年纪倏忽变成了三年纪。三年时光匆匆而过,感想杂陈,却只能记录下此时此刻此心境下的想法。
2013年8月26日,我第一次踏入香港,至今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了整整三年。三年以来,我在这里读书、毕业、工作,经历了前22年都未体会过的变动与挣扎。在这里见识了更宽广的世界,经历了更苦涩的困境,不停地重建并毁灭生活的计划与意义。
我总喜欢将香港称为“玻璃之城”,这是看过电影后浪漫的小执念,亦是我在这座由玻璃大楼拼凑而成,外表梦幻却内心脆弱的城市生活后对它最贴切的形容。
![]()
藏在烟雨中的香港第一高楼ICC
不是太迷港片和TVB的我,最浓郁的香港情怀就寄托在王家卫摇晃晦暗镜头下潮湿拥挤、混乱繁杂的街景中。于是抵港一个月后就去朝圣了著名的重庆大厦。
门前聚堆发小广告形色诡异的印度男,大厦内唤着“Beauty”随时试图拦路的黑人小哥,空气中浓郁的咖喱味儿混合着香料,再加上脑中盘亘着前些日余温未散的“案”,一踏进楼内就让人瞬间精神紧绷,仿佛几百米开外的维港灯火已被隔离于另一个世界。
![]()
然而在这种乍见不安的环境之下,这栋自给自足的建筑正展现着一个微缩的香港,展示着香港对多样文化和生活形态极大的包容性。正如同重庆大厦将100多个国家的文化碰撞裹挟于一栋外表破旧的大楼之内,香港这座城市也将每一个迥异个体的风光与挣扎隐藏在闪闪发光的玻璃大厦之下。我想除却购物、美食、发达社会的城市名片,这种包容和共荣这才是香港最让我着迷的地方。
在湾仔地铁站A3出口,天桥下排排坐着领取的伛偻中年瘾君子们,徘徊着终年端啤酒游荡于湾仔、形似“甘地”的枯槁大叔。弹吉他的小清新金发少女还在角落调音,丸子头帅哥已经和搭档开始了Hang drum和手鼓的表演。然而街头艺人的音乐却被举着话筒慷慨激昂宣传民主新生的政客议员盖了过去,但很少有人接过他发出的传单,就像趴在地上的残疾乞丐只收获了零星的几块硬币,毕竟路过的上班族都太忙了,没有时间驻足欣赏这一场生机勃勃的混搭表演。
![]()
下班时间的湾仔地铁站A3口总有各式各样的街头艺人在表演
而每周路过两次的我会花费10至20秒钟的时间将这幅略诡异的混搭秀记录下一个片段,我喜欢这样的碰撞与活力四射,正如维港和中环的夜色永远灯火通明。不同身份的人相安无事地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各行其是,施展着用力生活的欲望和姿态。我所热爱的这种极具戏剧张力的生活场景显示着包容,而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包容就是自由。
我的一位韩国学生,35岁左右的单身女子只身前往香港,她希望继续留港的原因是,在香港对女性来说拥有更平等的升职空间,有着不需喝酒应酬就能安稳工作升职的工作环境。她觉得,在香港人们更重视保留彼此私人生活的权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不必担心别人品头论足的声音干扰自己的选择。当然,有时这种不侵犯私人空间的克制会造成一种冷漠的表象,但我却愿意将它视为一种尊重,一种不必担心大龄未嫁、事业不体面、爱好古怪等任何背离社会期望的状态被扣上“不正常”的帽子。
所以,三年来,在这个逼仄狭小,拥挤喧嚣,整日穿梭于城市森林而望不见蓝天的城市里,除了身处“墙外”的信息自由,我感受到多样性和包容感所赋予每一个单独个体的自由,也期待自己能将这种自由和宽容赋予他人,不再对任何离经叛道的人事挑眉咂舌。
![]()
对我这种离家在外的边疆儿女来说,不管在哪里都是X漂。而作为“港漂”,不仅要忍受反人道的狭小居住空间、潮湿的环境、阶段性的蟑螂成灾,还要承受“轮子上的生活”。我在香港的3年间总共住过5个不同的住所,拉着行李,从沙田到蓝田到峻滢再到坑口最后又回到峻滢。轮子吱啦啦地划过地面,每搬一次家都好像在打怪升级,一次次地刷新着心理极限。
![]()
一家五口挤着住六七十平的房间是香港普通家庭的常态
沙田不到30平方的房间,厕所藏在厨房里,与室友合住了一个月1米2宽的床,最后练就了一身贴墙睡的本领。以至于后来独享那间还没我家厕所大的卧室时,竟也觉得无比满足。离开的前一个月这间老旧的房子蟑螂成灾,与朋友一同奋勇徒手徒脚歼灭几十只会飞的大蟑螂,感觉自己帅得脚底生风,但那只半夜从我脸上爬过的蟑螂最终还是击破了我最后的心理底线。
搬离蓝田的豪宅,为了和Cici住得近一些,打破了不与男生合租的底线。拉着一车行李忐忑地搬进那间极具男生宿舍脏乱特色的房间,打扫卫生、整理行李、独自拉着行李箱去宜家买生活用品,最后又累又无助地倒在4平米小房内的廉价床垫上被一堆无处挂置的衣服包围,一边哭一边给我爸打电话,叫嚷着“都没有人可以帮我”。与两个陌生男生的合租经历,非但没有上演众望所归的偶像剧狗血剧情,反而还需要随时忍受他们糟糕生活习惯而带来的多种生物的袭击。最终更是被临时通知要在生日当天搬走,给我措手不及当头一棒,瞬间陷入了将要流落街头的恐慌之中。
接着在最颠沛流离的本命年生日月,走投无路地搬进一间四个男生合租的蟑螂房,本以为可以如租约所言独享一套房子,却在与满屋子蟑螂和满布霉斑的黑乎乎墙壁为伍了几天之后依次与四个陌生男生合住了一个月。在这段不安稳的日子里,我妥协了一切自己对卫生和生活品质的要求,习惯了在成堆的包裹里和行李箱里找东西,甚至3分钟就能打包好所有每日生活的必需品立刻拖着箱子出门。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居无定所的漂泊和不安定感,在搬家和找新房子的痛苦过程中,无数次地想要打包回家,放弃这种咬牙的坚持。
![]()
也会在某个瞬间期待仰头望见某盏等自己回家的灯
每当向人讲起这一段段心酸的合租生活就油然而生一种悲壮之情,有点得意地感慨被supermommy娇惯多年的我竟能将这些一一承担下来。恐怕这种漂泊的生活状态是大部分X漂青年们想要逃离北上广的主要原因之一,毕竟《欢乐颂》这种合租乌托邦只是大部分X漂编剧们YY的所谓现实童话。但脱离了自我怜悯后冷静想想,那个毕业回家呆在爸妈身边整日享受假期生活当小公举的我,若穿越平行时空瞥见了这三年的在港生活,会不会依旧羡慕大于怜悯呢?
![]()
因为工作原因已不止一次动过辞职离开香港的念头,但始终因为摇摆不定的决心和对改变的恐惧而从未实现。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正式提交辞呈,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我的香港生活将定格于这第三个年头。和当初毕业离开北京时一样,原本寡淡却渐渐渗透进日常的感情全部都因为“离别”这个动作显得无比深刻。很多人问我喜不喜欢香港,对于这个问过自己很多遍的问题,已经在心里画满了勾勾叉叉,而糟糕的是,二者的数量始终旗鼓相当。
这三年,我习惯了3倍的步行速度,从当初走路被后边人催促,到现在对前边的挡路人发出不耐烦的咂舌声;在逼仄的小巷和高楼林立的街道中低头行走,而逐渐忘记了原来每日头顶也有晴朗的蓝色;将逛街视为最好的减压方式,在一年10个月的促销季中欢脱地用衣服塞满本来就不宽敞的小出租屋,然后把每月的工资原封不动地转去填补信用卡的大窟窿;三年来只凭着一句“唔該”在粤语环境里受白眼、闹笑话,。整个城市的高压和快速运转会对一个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可以明显感觉到自己正在变得不耐烦、急躁、自私冷漠。香港本地人总是自嘲香港生活是Hard模式,凡是能在香港生存下去的人都能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生存下去。
![]()
永远分割蓝天的高楼,如玻璃森林也如水泥牢笼
来香港前就看过冯唐感慨香港的空间狭小使得所有的生活服务设施高度集中。每当我短暂离开香港回家过节或外出旅行时,都会感慨香港恐怕是世界上生活最便利的城市。高效的城市管理、高素质的居民加上如此方便的生活设施,但凡在此生活过的人都会被惯坏,变成处处不满的挑剔欧巴桑。当我设想自己离开香港的生活时,就开始舍不得永远上盖的地铁、种类繁多又地道的世界美食、紧跟欧美的电影档期、贯穿中西的展览表演、肆无忌惮的特价买买买……
或许现在的香港已不是最好的香港,随着中港矛盾在年轻一代里日益尖锐,唱衰香港的声音越来越响。,却常常身不由己地在某些午间闲谈、FB新鲜事或与local学生的聊天中被莫名触碰到身份认同的痛点。有时我安慰自己这是成长背景和教育迥异造成的观念对立,然而一些带有侮辱性、嘲讽性的言论仍然令我不适,将我挡在融入这个城市生活血脉的大门之外。就像看过那部充满和谐点的金像奖最佳影片后的感受一样,我为这些愤怒却固步自封的年轻人感到遗憾,同情他们对未来生活的绝望,。
越来越多标题耸动唱衰香港的文章在社交网络上疯转,两极化的言论让我悲喜交加又唏嘘不已,像看着一个风光一世却被打入冷宫的妃子,人们曾经因为香港的特殊而为它带上耀眼的光环,现在又为这种特性的泯灭而写下大势已去的挽歌。
![]()
毕业工作后的两年中,我在无数个夜晚动了打包滚蛋回家的念头,又无数次举起要在此享乐人生、体验生活的大旗。于是这样的不满与不舍形成了势均力敌的拉扯,我的决心就像藏于薛定谔盒子里的猫,在我未离开或留下时就永远处于五五分的中间态。
![]()
终于断断续续写完这篇支离破碎的感想的晚上,我在办公室里修改着中英文简历,犹豫着该怎样五五分地投出它们。曾经热血参与过“那场运动”的同事正在用手机功放着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公选投票结果。
全香港履行了选举权的人们都关注着这个声调激昂却模糊的粤语新闻,而我坐在5米外用简历占卜自己与这座城市的缘分,然后把两年纪的标题里的数字改成“三”。
![]()
图片全部原创©Cici
本文来自个人微信公众号ONCE(ID: ciciandkiki)的投稿,原始文章请点击“阅读原文”,港漂圈授权刊登,如需转载请联络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