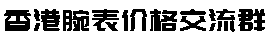侷住香港系列报道四:劏房,难说再见。
前言
据香港政府最新报告,全港20.97万人居于劏房等恶劣住所环境,而深水埗是全港劏房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民间组织与政府机构都致力于解决劏房人士的住房问题。然而,随着近年来劏房住户的不断增加,在短时间内彻底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并不现实。目前,社会各界力量主要集中于改善劏房住户现状。其中,香港的民间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物资帮助、进行心理关怀、协助申请相关福利、提供更多良心住房……但在土地资源方面,若无政府的支持,民间组织能做的实在有限。
“北斗星”与“萤火虫”
“香港现在基本找不出没有劏房的区域了,中环也有劏房。”SoCo资深社工戚居伟告诉我们,“我们会尽力帮助劏房住户改善生活,找到希望。”
在社工起源的西方国家,平均每1000人有一位社工。而在香港,平均每562人即有一位社工。香港对社工采取严格资格认证和强制注册管理,社工专业毕业、完成800小时的社会工作实习才能取得文凭。
在香港,社工享有“北斗星”的美誉,他们为正处人生低潮、黑暗中的受助者指引道路,提供光亮。但更多时候,社工们更觉自己是“萤火虫”。不及北斗星的万丈光芒,萤火虫只提供点点微光引路,却是社区民众的同行者。
社工们也是劏房住户们生活的重要角色。第一次见到我们时,劏房住户齐福俊曾问我们是哪里的社工。在他眼中,社工上门探访劏房住户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施姑娘(姑娘”:香港对女性社工的称呼)真是我的大恩人!”来自山西的齐福俊满怀感激之情地告诉我们。前几年刚移民到香港时,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举目无亲的他第一次拨打了社工的电话,当时关怀无家者协会(下文简称“无家者协会”)的施姑娘和另外一名社工一起打车,将他送到了医院。齐福俊前后三次来港,三次都经施姑娘的帮助找到了住所。而原则上,无家者协会的社工只能为受助者提供一次住宿机会。
提起施姑娘,齐福俊反复向我们强调,“她真的是个特别好的人!”他从抽屉里拿出他写给施姑娘的感谢信,信中写道:“身患重病的人在无助中等待光明,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是你为我伸出一双手,点亮了一盏灯。”
遗憾的是,在施姑娘换工作后,齐福俊弄丢了她的联系方式,没能将信寄出。“怎么就丢了呢,我真想好好感谢她,请她吃顿饭”,说完,齐福俊挠着头,语气变得有些懊恼。
| 齐福俊写给施姑娘的信 |
安仔如今最期待收到社工们的表演邀请。收到无家者协会春宴邀请的那天,他把自己好好打理了一番,晚会7点开始,他5点半就到了酒店。社工毛卓贤与他同台演出,并把工作日常写成歌词,用嘻哈唱法唱了出来:“安仔细细个,已经钟意唱歌,在北河街街市外面,跳舞好似郑伊健。……有几多风雨,依旧继续唱。”安仔戴着墨镜,身体随着节奏律动着,手高高地指向天空。
这是安仔第二次公开表演,他第一次表演是在一个多月前SoCo的慈善晚宴上。SoCo的资深社工施丽珊与安仔已经认识了三、四年。筹备晚会时,她第一时间给安仔打了电话,“有晚会哦,你不是爱唱歌吗?来表演吧。”她还给爱打鼓的伦叔也打了电话:“你来晚会打鼓啦,不过只能表演一首喔。”施丽珊的性格直爽,给住户们打电话时一点也不客套,就像在和再亲近不过的人聊天。
| 安仔与伦叔合作表演 |
除了在心理层面上关怀劏房住户,社工们还在物质层面上帮助他们。安仔在社工毛卓贤的介绍下找到了现在的工作,他现在也在轮候公屋,而申请公屋的一切事项,都是社工帮他完成的。“申请公屋太复杂了,我弄不懂”,安仔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不仅是安仔,我们接触的许多采访对象都告诉我们,是社工在帮助他们申请公屋。香港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的社工洪一兰说:“申请公屋需要很多程序,很多劏房住户,特别是新移民住户都对这些不太了解。”
遥望公屋
“取消绿置居,公屋不能卖!基层要公屋,拒绝做楼奴!”
2月8日,一阵阵口号声在何文田爱民社区会堂门口的空地回响。这里聚集了一大群人,这些都是由社工组织起来的劏房住户,他们中有人正分发传单,向行人解释他们的主张,有人则高举着红色横幅晃动,吸引旁人的注意。
| 劏房住户请愿 |
绿置居,是香港政府提供的资助自置居所的一种。市民可以用低于市价几成的价格购入资助自置居所。这些低价房屋不仅能照顾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也能让公屋住户在购买房屋后将公屋腾出给其他人。香港政府提供的资助自置居所主要是居屋,而绿置居的定价比居屋更低。早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曾表示,公屋数量已足够照顾基层家庭的需要,日后可以把大部分新建公屋转作“绿置居”。
几家媒体的记者举着镜头走向人群,一个穿着灰色外套的中年男子主动迎上镜头接受采访:“我认为政府的政策有问题,为公屋里的人提供绿置居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政府不应占用公屋的资源。”灰衣男子姓李,是这次请愿活动中与政府对话的主要发言人。
李先生一家四口住在深水埗青山道的劏房里。这一天,李先生特意向工作单位请了假,带着一群同样住劏房的街坊们来到这里,他们想向香港房屋委员会委员黄远辉请愿,表达他们的住房诉求。
香港民主民生协进会(简称民协)前主席、前议员冯检基认为,政府的绿置居政策会影响到公屋的流动性,从而令公屋的供应量下降。“原本住在公屋的租户会因购置了房屋而搬走,他们的公屋会腾出给正在轮候的人。但将公屋转化为绿置居,可流动的公屋总数就会减少。”
最新公布的2017年国际楼价负担能力报告显示,香港连续第八年登上全球楼价最难负担城市之首。一个标准家庭必须维持零支出状态(不吃不喝没零花)达19.4年,方能买得起一个住宅单位。
“香港的房价不是比较贵,是好鬼(粤语,意指“非常”)贵”, SoCo资深社工戚居伟耸耸肩,幽默地说。在九龙城,一间约为20平方米的高层公寓,每平方米的售价为27.9万元港币。
在高房价的现实下,香港普通人只能遵循“公屋-居屋-私楼”的置业阶梯——先住进政府租金低廉的公屋,然后攒钱购置属于自己的居屋,等有足够积蓄再换一套开发商投资建设的私楼。
而劏房住户们只求能搬进公屋。公屋人均居住面积13.2平米,相对平均住房面积仅5.3平米的劏房而言,已宽敞了许多;更重要的是,公屋的租金远远低于市价。伦叔现在不到2平米的板间房租金1800港币,而他17平米的公屋月租才900港币左右。
在我们的采访对象中,目前只有64岁的伦叔即将搬进公屋,为了这一天,伦叔等了近四年。而张女士的邻居在轮候了七、八年后,今年一月才搬去了公屋。
“排公屋的人问我们还要等多久,可我们完全回答不了”,无家者协会的社工毛卓贤望着我们苦笑。目前,香港的公屋轮候时间远超政府“三年上楼”的承诺。现实生活中,与张女士邻居一样等候了七、八年的人比比皆是。
外来移民的住房需求,以及香港本土家庭小规模化的趋势,是推高劏房与公屋申请数量的重要因素。香港房屋委员会和房屋署的数据显示,公屋的申请数量由2012年中的106100宗,增加至2017年底的155100宗。截至2017年12月底,共有28.29万个家庭及个人在轮候公屋。而政府2017年定下的“建造19000个公屋单位”的计划,如今只完成了11276个单位。
“公屋的兴建需要经过很多法定程序的审批,从规划、咨询、兴建到最后落实都需要很长时间”,香港房屋委员会委员黄远辉解释道。
| 黄远辉与请愿群众合影 |
香港土地资源有限,较多公屋的土地都由填海而来。从1985年到2000年,香港政府填海3000公顷,但近些年来,社会上关于环保的呼声愈来愈大,政府的填海计划需要得到、海岸管理局、城市规划委员会等多个部门的批准,“填海工作得不到社会的支持,用于兴建公屋的土地就不够了,公屋建得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土地资源不足”,黄远辉说。
“政府做得太少了”
“香港土地资源有限,无论交通、医疗还是休息空间,需求都在增加。”对于低收入人士对公屋的需求,黄远辉十分理解。但他坦言,香港的土地资源还需要用来满足经济发展的其他需求。
“我们也希望一觉睡醒,劏房就不存在了”,香港资深社工戚居伟的眼睛一睁一合,作出睡眠状,“但这不可能。”戚居伟承认,在香港迫切的居住环境下,劏房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他认为政府可以做得更多。
今年是李先生在青山道的劏房里居住的第6年。搬来的第二年,劏房2650港币的房租就变成了2950港币,现在则涨到了3650港币。“这样的涨幅算小了。”李先生说,他有朋友在第二年就被加租了800港币。李先生是厨师,每个月一万左右的月薪,减去加上水电费在内4500港币左右的房租,再减去两个儿子每个月2500港币的书本费,每个月的结余所剩无多。
“劏房住户的薪金涨幅远不及租金的涨幅,他们只能越住越差、越住越小。” SoCo的资深社工施丽珊认为,劏房住户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2002年之前,香港曾实施过租务管制,政府会对租金的涨幅进行控制;但在经济萧条时,香港取消了这一制度。租务制度的取消使得许多劏房住户在忍受狭小的居住环境外,还不得不面对随意上涨的房租。除此之外,也造成了业主随意赶走租户、租户遭业主滥收水电费的情况。
“租务管制事关众多业主的利益,政府不想得罪业主,而且中有许多中层人士,想要通过相关的立法很困难。”对于租务管制的缺失,施丽珊有自己的看法。,香港目前正处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占据主导地位,财团具有较大的话语权。
| SOCO资深社工施丽珊女士 |
尽管知道恢复租务管制很不容易,施丽珊和众多社会人士仍一直向政府进行倡议。SoCo每次与政府进行会谈时都会向政府提出恢复租务制度的请求,而全港租客大联盟则在每年的7月9日进行游行,要求政府重设“租管条例”。
在住房问题上,香港政府一直坚持市场自由调控。对于居住环境恶劣的住户,。,面对大众要求取缔笼屋的需求,。其他方面,政府则以“市民需要”的理由拒绝介入。
在黄远辉看来,恢复租务管制没有那么容易。“租务管制会导致出租单位的减少,从而导致租金的上涨,这也是租务管制当初被废除的原因。”他认为即使恢复了租务管制,这一制度也难以惠及所有需要帮助的租户,“在市场化的租务市场,行政上的手段往往很难达到想要的效果。”身为退休的银行家,深谙政策与市场关系的黄远辉感到很无奈。
而对于这一层顾忌,施丽珊则认为政府可以借鉴国外的物业税,“不想交税的业主自然会将房屋出租”,她说道。
除了致力于解决劏房住户的租房窘境,社会力量还积极探索住房新形式,希望能提供更舒适的低廉住所。“要有光”组织推出了“光屋”模式,为有需要人士提供了人均不少于7平方米,租期不超过三年的低价租房。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下文简称社联)则发起了“社会房屋共享计划”,他们在社会上寻找愿意低于市价出租房屋的良心业主。
| “要有光”网站首页 |
而在政府方面,针对近些年不断恶化的劏房问题,特首林郑月娥在上台后的首份施政报告中提出了过渡性房屋计划(即提供环境更舒适、价格更低廉的短期住房),希望借此缓解处于恶劣居住环境人士的困境。但政府声明其只扮演辅助角色。
施丽珊认为政府在社会房屋上做的太少了,“在荷兰,政府会提供多种协助,包括提供低租金的空置地,提供水源、电力、道路等基础建设、低息借贷等。而香港政府目前只提供资金,虽然政府也授权了社联统筹工作,但这样很难解决问题。”施丽珊苦笑着摇摇头。
黄远辉则认为香港政府职责范围有限,“政府的确不能够完全涵盖对资助房屋有需求的家庭,所以社会上才会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做着更加细致的工作,来完成政府不能帮到的状况,特别是在房屋方面。”
土地资源先天不足,而争取土地建造公屋的道路阻碍重重;在改善劏房问题现状的议题上,社会组织自觉力有不逮,政府则声称鞭长莫及。在张定准教授看来,香港劏房问题短时间内难以解决,想要依靠香港政府建立全面的住房保障措施也是不现实的。看来,在和劏房说“再见”的征途上, 香港还是长路漫漫。
(本文转自公众号牛犊走笔)
文字 | 苏月月 林敏儿
图片 | 番茄侷蛋小组
版式 | 石晓曼 刘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