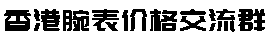最神奇的实验
The Most Amazing Experiment
作者:罗伯特•兰萨,鲍勃•贝曼
Robert Lanza and Bob Berman
摘自《生物中心主义》
作者介绍:
罗伯特•兰萨(Robert Lanza,医学博士)被认为是世界科学家中的一位领军人物。现任先进细胞科技公司的首席科学官及维克森林大学医学院兼职教授。兰萨博士被称为“科学界的比尔•盖茨”。他获奖无数,入选《美国名人录》、《世界名人录》等。他的导师们说他是个“天才”、一个“离经叛道的思想家”,甚至把他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
鲍勃•贝曼(Bob Berman)是位美国天文学家、作家和科学普及者。他在纽约州伍德斯托克的家中开办了“眺望天文台”(Overlook Observatory)。他也曾于1996至2000年间在马利蒙•曼哈顿文理学院担任天文学副教授,并曾在“CBS清晨”、“今日秀”和“大卫•莱特曼的午夜场”等节目当中出现。
很不幸,量子理论已经成为试图证明各种新时代谬论的万能措辞。很多书籍的作者做出了关于“时间旅行”和“思想控制”的荒谬断言。他们试图用量子理论作为依据,但是,极有可能的是,对物理学,他们连最简单的认识都没有,而对于量子理论,即使是最基本的东西,他们也不能说出个所以然。2014年的流行电影《我们到底知道什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电影一开始就声称,量子理论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这一点当然毋庸置疑。但是,接下来,在没有作任何解释或详细说明的情况下,它就声称,这证明人可以回到过去,或“选择你想要的现实”。
量子理论并没有下过这样的断言。它处理的是概率,是粒子可能出现的位置,以及它们可能具有的行为。虽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对于微量的光与物质而言,其行为的改变确实依赖于它们是否被观测,被观测的粒子看起来确实令人讶异地影响了其他粒子过去的行为,但这完全不意味着人类可以回到过去,或者可以左右自己的历史。
由于量子理论在大范围内被“泛化”使用,再加上生物中心论的范式转移宗旨(译注:“范式转移”是指,依据某一领域的新成果,对其采取全新的视角),采用量子理论作为证据,可能会使质疑者皱起眉头。基于这一原因,非常重要的是让读者对有关量子理论的真实实验有某种真正的理解,并掌握它们的真正结论,而不是那些经常与之硬扯在一起的荒谬可笑的断言。对于那些稍有一点耐心的读者,本章提供了关于物理学历史上最著名,最惊人实验的最新版本,这是一种改变人生的认识。
这一难以置信的“双缝”实验,几十年中一直在被反复地进行。它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宇宙观,并且为生物中心论提供了支持。本文将要描述的这个特定版本,是对发表在2002年《物理评论A 》中一个实验(Physical Review A,65,033818)的概述。然而,实际上,它只是过去75年中被反复演示着的另一种经过“微调”的版本。
这一切始于20世纪早期,当时的物理学家们仍挣扎于一个古老的问题:光是由称为“光子”的粒子组成,还是一种“能量波”?牛顿相信“粒子论”。但是,到了19世纪晚期,“波”的观点看起来好像更为合理。在那些早期的时光里,一些物理学家富有远见并正确地认识到,即使是实体物质,也同样可能具有“波动性”。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使用的“源”可以是光,也可以是粒子。在传统的双缝实验中,粒子通常是电子,因为它们小而“基本”(它们不能被分解成其他东西),同时易于射向远距离目标;比如,传统的电视机中,就是将电子射向荧光屏。我们的实验从光瞄准检测屏(或称为“接收屏”)开始。然而,在到达检测屏之前,光必须首先穿过一个具有两个孔(或狭缝)的遮挡屏(或称为“双缝屏”)。我们可以同时发射一束光,也可以每次仅发射一个不可分割的光子——结果都一样。每个光子从左边或右边缝隙穿越而过的概率各为50%。按照逻辑来说,如果将光子看作是粒子,一段时间之后,所有这些发射出去的光子“子弹”的“击中点”,应该在检测屏上形成这样的图案:,而在这一“优先位置”的边缘,只接收到少量的光子。这是因为,以光源为出发点,从狭缝穿越而过的路径,几乎都是指向正前方。概率规则告诉我们,接收屏上看到的应该是这样一簇光的“落点”:
如果将结果绘制成图表的形式(其中,竖轴显示的是击中次数,横轴显示的是检测屏上的位置),预期的结果是:,而有少量落在其边缘,所形成的曲线如下图所示:(译注:本文的图表中所标数据的测量方式,以及具体试验装置的示意图,在稍后的段落中有简单介绍,详细说明请直接参阅:Physical Review A,65,033818)
然而,这不是我们实际得到的结果。在如此所做的实验中(上个世纪,我们已经做了数千次),我们发现,光子产生的是这样一种奇怪的图案:
将结果绘制成图表,光子的落点看上去是这样的:
理论上说,围绕着主峰的两个稍小侧峰应该是对称的。在实际中,我们应对的是概率和单个光子位置的问题,所以,结果往往会与理想情况有一点偏离。但不管怎样,此处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图形?
答案是,如果光是由波,而不是粒子组成,而这正应当是我们所期待的结果。水波的相互碰撞和干扰会产生干涉条纹。如果你同时把两块鹅卵石扔到池塘,一个波和另一个相遇时,都会使一些位置的水位高于正常值,而其他一些位置的水位则会低于正常值。在有些地方,两个相遇的波会相互“增援”,而在另一些地方,如果一个波的波峰遇到了另一个波的波谷,它们则会相互抵消。
在二十世纪初期得到的这种干涉图样只能由波所导致,这向物理学家表明,光是一种“波”,或,至少在进行实验时,它表现为波的行为。神奇而诱人的是,当像电子这样的实体物质在实验中被作为“源”使用时,物理学家们得到了完全相同的结果。实体粒子也具有波的性质!所以,从一开始,双缝实验就提供了关于“实在”本质的令人吃惊的信息。实体物质具有波的性质!
不幸或幸运的是,这只是开胃菜。很少有人意识到,真正离奇的事刚刚开始。第一件怪事,是每次只允许一个电子(或一个光子)单独穿越实验装置的情况。实验中,电子或光子一个接一个地穿过,每一个都被单独检测到(即,在接收屏上出现一个撞击点),然而,当数量足够多的电子或光子完成了它们的旅程后,这些撞击点所形成的,是(与大量电子或光子同时穿越装置时所产生的)完全相同的干涉图样。但是,这怎么可能?这些电子或者光子是与什么产生了干涉?当每次只有一个单个的不可分割的客体存在时,我们怎么能得到干涉图样呢?
单个光子撞击检测屏
第二个光子撞击检测屏
第三个光子撞击检测屏
莫名其妙的是,这些单个的光子的“击点”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干涉图案!
对于此问题,从来就没有给出过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答案。疯狂的想法不断涌现。是否有可能存在着另外的电子或光子,它们来自于一个平行宇宙中的“邻居”,来自于另一位做着同样事情的实验者?他们的电子有可能与我们的电子发生干涉吗?这太牵强了,很少会有人相信它。
对于我们为什么看到一种干涉图样,通常解释是:光子或电子在遇到双缝时,它们有两种选择。在被观察之前,它们并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实体,真实地存在于一个确定的位置;直至撞击到最终的检测屏,它们才被观察到。所以,当到达狭缝时,它们“行使”了自己做两种选择的概率自由。尽管实际的电子或光子是不可分割的,并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自我分裂,然而,当它们作为“概率波”存在时,情况就全然不同。因此,当从狭缝中“穿越而过”的并不是真正的实体,而仅仅是概率时,单个光子的概率波自己与自己发生了干涉!当足够数量的光子或电子穿过后,我们看到了整体的干涉图样,就像所有概率“凝固”成了一种真正的实体“波动”,遇到接收屏所产生的观察到的结果。
确实不可思议,但很明确,这就是现实世界的运作方式。而且,这还只是“量子怪事”的开始。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提到的,量子理论中有个被称为“互补”的原则,这个原则说:我们可以把观察目标作为具有某种,或另一种特性的对象去做测量——或者它占据一个位置,或者具有另外某种特性,但绝不能是共具两种特性的对象。这取决于人们在观测什么,以及所用的是哪种测量设备。
现在,假设我们想要知道,一个给定的电子或光子,在飞往检测屏的路途中穿过了哪条狭缝。这是一个足够合理的问题,并且很容易找出答案。我们可以利用“偏振光”(意思是,光波的振动方向或是水平,或是垂直,或是缓慢旋转着)。如果在使用这种偏振光的过程中,其他实验条件都没有改变,那么,我们得到的结果和前文中完全一样。但这次,我们要确定,光子从哪条狭缝中穿过。我们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装置来实现这一目的,但在本实验中,我们将会在每条狭缝前加上一个“四分之一波片”(“QWP”)。每一个四分之一波片都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改变了光的偏振方向。我们可以在如前所述的检测屏前安放一台检测器,用来检测射入光子的偏振方向。通过记录光子被检测到的偏振方向,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从哪条狭缝中穿过。
然后,我们重新做这个实验,每次只射出一个光子,它穿过了狭缝;但与前文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知道每个光子从哪条狭缝中穿过。这即刻导致了实验结果引人注目的改变。尽管两块QWP除了使光子的偏振发生了变换之外,并没有对光子做任何改变,但现在我们得到的,不再是干涉图形。(光子偏振的改变对实验无任何“妨害”,稍后我们会证明,这一变化不是由QWP引起的。)现在曲线突然发生了变化,它所呈现的,正好是我们将光子看作粒子时所期待的那种样子:
一定发生了些什么。原来,正是这种测量行为,这种对每一个光子的路径的获取,将光子在到达检测屏之前保持“模糊”和“不确定”的状态,从而可以同时穿过两条狭缝的“自由”破坏掉了。光子的“波函数”必定在我们的观测设备,即两块QWP之处,在它“选择”成为一个粒子,并穿过其中一条狭缝的即刻,发生了坍缩。在失去了它的模糊的、概率性的“不真实”状态的同时,光子立即失去了波的性质。但是,为什么光子选择了使它的波函数坍缩?它是怎么知道,我们,也就是观察者,会知道它从哪条狭缝中穿过呢?
过去一个世纪里,拥有最伟大头脑的人们无数次地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但全都失败了。仅仅是我们对光子或电子路径的“了知”,就会导致它们成为确定的实体。当然,物理学家也怀疑过,这一古怪的现象,是否是由QWP(或实验中使用过的其他路径观测装置)与光子之间的某种相互作用引起的。但情况并非如此。种类完全不同的路径观测装置曾被使用过,它们之中没有任何一种以任何方式对光子产生过干扰;然而我们总是会失去干涉图形。多年后,人们得出的底线结论是:若想在得到路径信息的“同时”,也得到由能量波引起的干涉图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让我们回到量子理论中的互补性原理:你可以测量并了知“一对”特性中的一种,但决不可能同时了知二者。如果你完全知道了其中一种,那么,你对另一种将一无所知。为消除你对那些四分之一波片万一会有的怀疑,附带再说一次,在所有使用过这些波片的其他情境中,包括终点处没有安放检测偏振方向装置的双缝实验在内,仅仅改变光子偏振方向的这一行为,从来不会对干涉图样的形成产生丝毫影响。
好吧,现在,让我们换一个问题。如同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自然界中存在着“纠缠粒子对”,即,成对的“微量光”(光子)或其他物质的粒子;它们一起生成,因而,根据量子理论,具有“共享波函数”。它们可以飞至彼此相距很远(甚至跨越银河系)的地方,但仍能保持这种关系,以及这种彼此的“互知”。如果其中一个以任何方式被干扰,因而,失去了它“一切皆可能”的特性,并必须立即决定实体化,比如,垂直偏振态,那么它的孪生兄弟也将立即实体化,成为水平偏振态。如果其中一个变成了自旋向上的电子,那么其孪生兄弟也会变,但是,其自旋是向下的。它们永远以互补的方式关联在一起。
然后,我们利用一个装置,将“纠缠着”的孪生粒子向不同方向射出。实验者可以使用一种特定的,称为β-硼酸钡(BBO)的晶体产生纠缠光子对。在晶体内部,来自于激光的一个高能量紫光光子被转换成两个红光光子,每一个携带着紫光光子原有能量的一半(其波长为紫光的两倍),所以,总能量既没增多也没减少。这两个处于纠缠态的光子,在产生之后被向着不同的方向射出。我们将它们的路径称为P和S(沿着这两条路径飞行的光子也分别称为“光子P”和“光子S”)。
实验的第一步,将不去检测光子从哪条狭缝中穿过。现在的实验与上文所描述的唯一不同点,就是我们添加了一个“符合计数器”。它的作用是使我们只有在光子P撞击到检测器Dp的情况下,才能测量S光子的偏振方向。孪生光子中的其中一个(光子S)穿过双缝,而另一个(光子P)直接飞向第二个检测器。只有当两个检测器在近乎同一时间检测到撞击,我们才知道两个孪生光子都已经完成了它们的行程。只有在那时,我们的设备才会记录下某种数据。所得到的结果,正是我们熟悉的干涉图样:
这是说得通的。我们没有获取到任何有关光子或电子是从哪条狭缝中穿过的信息,所以这些客体仍保持为概率波。
但现在让我们捣一点乱。首先,我们要重新加上那些四分之一波片,以便能够知道,光子沿着路径S行进时,穿过的是哪条狭缝。
正如预期的那样,现在,干涉图样消失了,替代它的,是“粒子类”的图样,即单峰型曲线。
实验进行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不错。但是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破坏掉我们观测光子S从哪条狭缝中穿过的能力,但不以任何方式干扰到这些光子。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光子P的路径上,距离S路径很远的地方,放置一个偏振窗。这个偏振窗将使第二个检测器失去所起到的“符合记录”作用。它将只检测到部分的光子,并有效地把符合信号搅乱。由于符合计数器的基本作用是在一对孪生光子的行程结束时作提示,现在它已经彻底地失效了。整个装置不可能再让我们知道沿着路径S行进的单个光子穿过的是哪条狭缝,因为我们无法将它与另一个孪生光子作比较(因为在没有符合计数器“允许”的情况下,任何数据都不会记录下来)。让我们明确一下:我们保留了对光子S起作用的四分之一波片。我们所做的仅仅是对光子P的路径做了干预,从而“消除”了我们知道光子S所经过的是哪条缝隙的能力。(总的来说,整套装置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记录下撞击:当光子的偏振方向在检测器S处被检测到,与此同时,符合计数器告诉我们,检测器P检测到了另一孪生光子的不论是否匹配的偏振方向)结果如下图所示:
它们再度呈现为波。干涉图形得到了恢复。沿着路径S行进的光子或电子在检测器上的撞击位置变了。然而,我们对这些光子的路径(从最初在晶体中产生出它们,直到最终到达的检测器的全程中)没有做过任何事情。我们甚至让四分之一波片都留在了原处。我们所做的只是去“打扰”远处的孪生光子,以便破坏我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唯一的变化出现在我们的意识中。沿着路径S行进的光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在离它们路径这么远的地方放置了偏振窗?量子理论告诉我们:即使把信息破坏器放到宇宙的另一端,我们还是会得到相同的结果。(而且,顺便说一句,这证明:光子从波变成粒子,并改变了它们在检测器上的撞击点,并不是由四分之一波片引起。即使把四分之一波片保留在原处,我们现在得到的仍然是干涉图样。看来,那些光子或电子唯一“关注”的,是我们对它们的“知晓”。仅此一点就会影响到它们的行为。)
不错,这确实很奇怪。然而,这些结果每次都出现,无一例外。它们在告诉我们,观察者决定“外在”物体的物理行为。还有比这更奇怪的吗?稍等,我们将尝试一点更“激进”的东西,一个2002年才首次进行的实验。直至现在,我们谈到的实验所涉及的,是通过扰乱另一条路径中的光子P,然后再检测它的孪生光子S,以此“抹掉”了 S 从“哪条狭缝”中通过的信息。也许光子P和S之间发生了某种交流,使得光子S知道了我们将获得什么信息,因而,为它去做选择开了绿灯——是成为“粒子”还是“波”,是生成还是不生成干涉图样。也许当光子P遇到偏振窗时,它向光子S发出了一条速度无限快的IM(即时消息),所以光子S知道了它必须立即“物化”为一个真正的实体;它必须是一个粒子,因为只有粒子才能只从一条狭缝中穿过,而不是同时穿过两条。结果就是:没有干涉图样。
为了核实一下是否真的如此,我们要做另一件事。首先,我们要延长光子P与它的检测器之间的距离,使得它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到达那里。这样,沿着路线S行进的光子会先到达它们的检测器。但奇怪的是,结果并没有改变!当我们在路径S的双缝处插入四分之一波片时,干涉图样消失了;当我们在路径P插入偏振窗,并失去通过符合测量来确定光子S穿过了哪条狭缝的能力时,干涉图样又恢复了。但是,这怎么可能呢?沿着路径S行进的光子已经完成了它们的旅程。它们要么穿过其中一条狭缝,要么同时穿过两条;它们的“波函数”要么发生了坍缩,成为了粒子,要么没有坍缩。游戏已经结束,动作已经完结。它们在其孪生光子P遇到偏振窗(它“劫走”了我们关于光子S路径的信息)之前,就已经撞击了终点处的检测屏。
这些S光子以某种方式知道了我们是否会在未来获得它们的路径信息。在其处于远方的孪生光子与我们的偏振窗相遇之前,它们就决定不坍缩为粒子。(另外,如果我们拿走路径P上的偏振窗,光子S会突然恢复为“粒子”,这同样是在P光子到达它们的检测器,并触发符合计数器之前。)不知怎的,光子S知道“哪条狭缝”的信息是否将会被抹除,即使它和它的孪生光子中的任何一者都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个抹除机制。它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表现为干涉行为,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安全地保持其模糊如幽灵般的,能同时经过两条狭缝的状态;因为它显然知道远距离外的光子P最终一定会穿过偏振窗,而这带来的结果就是阻止我们知道它会穿过哪条狭缝。
无论我们如何设计实验都于事无妨。我们的头脑具有或缺乏对它的了知,是决定这些光子(或物质)行为的唯一的因素。同时,这也迫使我们对时间和空间产生疑惑。如果一对孪生光子在信息得到之前就采取行动,并且能跨越距离,就像它们之间没有任何间隔一样进行即时信息交流,那么,时间或空间中的任何一者会是真实的吗?
一次又一次,实验结果都证实了量子理论所提出的观察者依赖效应。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物理学家进行了一项实验。在量子世界,它相当于示范了“被盯着的锅烧不开”。一位名为Peter Coveney的研究者说道:“看来,盯着一个原子看的行为能够阻止它发生变化。”(从理论上讲,如果一个核弹被足够专注地观看,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持续不断地每隔百万兆分之一秒对它的原子查看一次,它就不会爆炸。这也是支持“物理世界的结构,特别是数量微小的物质和能量,受人类观察影响”观点的另一个实验。)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量子理论学家表明,原则上,一个原子如果被不间断地观察着,它就无法改变自己的能量状态。现在,为了测试这个理论,NIST的一群激光实验人员用磁场(可以比喻为“锅”)将一团带正电的铍离子(“水”)固定在一个位置。他们以射频场的形式对锅“加热”,这会将原子从低能态激发至高能态。这一转变的进行通常需要耗时四分之一秒。然而,当研究人员持续不断地利用激光器发射的短脉冲光,每隔四毫秒对那些原子进行一次检查时,尽管外力正在驱动它们向高能态转变,但这种转变却无法发生。看起来似乎是检测的过程给了原子一个“小小的推动”,迫使它们回到低能态,其效果是将系统复位为零。在日常感官意识的经典世界中并无类似的现象,它显然是观测行为带来的作用。
神秘吗?奇怪吗?很难相信这些效应是真实的。这相当地令人惊奇。在上个世纪初,当量子物理还处于它的早期探索阶段时,一些物理学家甚至将这些实验发现视作不可能或“无或然性”事件,因而将其排除在严肃对待的范围之外。回想起爱因斯坦对于一些实验的反应,令人颇感奇怪:“我知道这件事无懈可击,但在我看来,它包含着一定的不合理性。”
只有在随着量子物理学的问世,客观论日渐式微时,科学家们才开始重新审视那个老问题:是否有可能将世界理解为心灵的某种形式。爱因斯坦在从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走向他位于Mercer Street的家的路上,,他是否真的相信月亮只有在他看着的时候才存在,以此来说明自己对客观、外在世界持续的着迷和怀疑。自那时起,物理学家们就开始分析和修订他们的公式,妄图得到自然法则的一种表述,这种表述不以任何方式依赖于观察者的境况。事实上,尤金•维格纳,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曾说道:“在不涉及观察者意识的情况下,不可能以完全一致的方式构建物理学法则。”所以,当量子理论表明意识必须被纳入其中的时候,它实际上是默许了,心灵所包含的才是终极的实相;而且,只有通过观察行为,才能将形态和结构赋予现实——无论是草地上的蒲公英,还是太阳、风,抑或是雨。
文章来源:
http://www.robertlanza.com/is-death-an-illusion-evidence-suggests-death-isnt-the-end/
原文发布日期:2009.04.14
智悲翻译中心 译竟于2016.01.08
翻译:Linda
一校:益辰
二校:圆阳
终审:圆恩